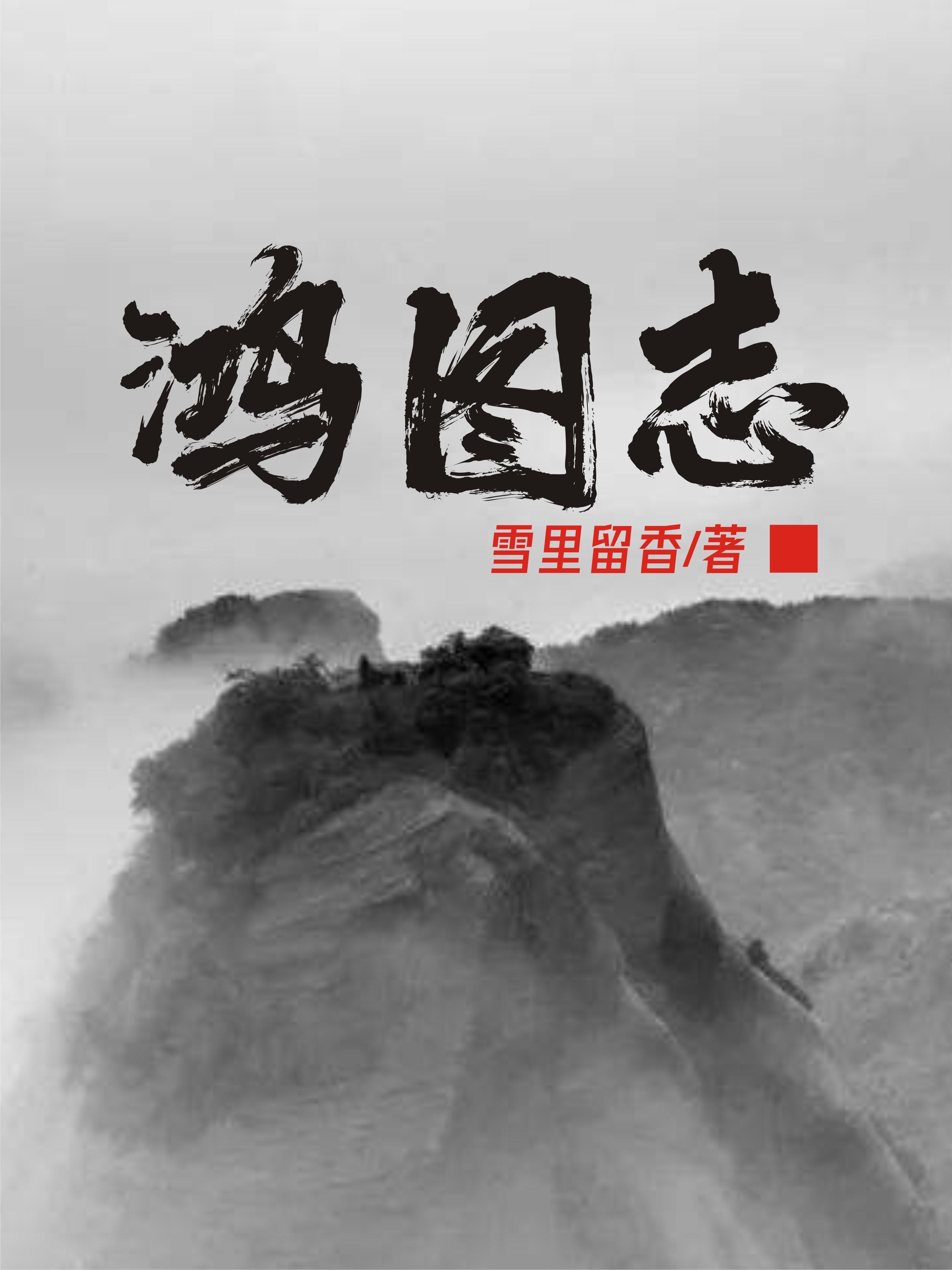极品中文>娇姝难藏 > 第417章(第1页)
第417章(第1页)
沈翊把闻姝的手指揉搓热了,掀开被子下床,“这个不急,我还得与岳父商量一下。”
说到“岳父”,沈翊揶揄地笑了一下。
闻姝嗔了他一眼,“又打什么坏主意。”
“先用早膳,饿了。”沈翊温柔的抚了抚她的长发。
但闻姝只简单的挽了一下,用玉簪别住,松松散散,他这一碰,闻姝的长发便散了下来。
闻姝瞪着他,“看你干的好事。”
沈翊笑着讨饶,“我给你挽起来。”
“你会嘛?”闻姝不大信。
“我试试。”沈翊拉着她坐到梳妆台前,铜镜中的闻姝不施粉黛,已然倾城,从小看到大,沈翊仍会因为女子镜中的一个回眸心动不已。
沈翊没为她挽过发,但经常见竹夏她们给闻姝梳妆,也学到了点精髓,勉强挽了起来,就是有点歪,第一次挽发已经不错了。
闻姝对着铜镜扬起唇角,“夫君手挺巧。”
沈翊弯腰与镜中的闻姝对视,“以后我多学学,给你挽发描眉。”
顺安帝一去,颠沛流离的日子终于结束,他们即将开始全新的稳定的生活。
闻姝同样在期待这样的生活,“好。”
用过早膳,闻姝想着还是进宫点个卯,在人前露个脸,月露赶着回来了,说善兰堂一切都好。
闻姝坐上马车,啧叹一声,“善兰堂有绮云在,我倒放心,原本还说等咱们回来就可以看见绮云和周大人成亲了,可国丧百日,算起来,得明年了。”
陶绮云与周羡青这事差不多就定了,卫如黛与贺随之间还隔着一层窗户纸,也不知道有没有结果。
“暖和起来办正好。”沈翊想了想,问她,“陶姑娘成亲后,你还打算留她给你帮忙吗?”
闻姝:“得看她愿不愿意,我想培养一批女官,你呢,打算给周大人什么赏赐?”
周羡青和贺随都是一开始跟着沈翊的,沈翊若是登基,定然要封赏,嘉奖追随之功。
“暂时没定,除了他和贺随,我在想徐音尘该给个什么赏。”沈翊并非忘恩负义之辈,最初徐音尘在魏六那件事上立了功,给魏家撕开了一道口子,因此即便后来两人渐行渐远,沈翊还是记着的。
闻姝没纠结,直言道:“按照规矩来,该怎么给就怎么给,如黛不会介意。”
自从如黛得知徐音尘续弦,神情低落过两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了,无论过往如何,大家都需要往前走,既然没有缘分,就不必再念念不忘。
沈翊微微颔首,“行,我再斟酌一二。”
路上正说着,入了宫,吏部尚书求见沈翊,拿了封折子过来,“徐大人以母亲年迈为由,想要辞官回家侍奉母亲终老。”
吏部尚书知道徐音尘是沈翊的人,因此不敢擅作主张。
沈翊翻着折子,徐音尘的字很有风骨,在善兰堂读书时,便很用心,褚先生也常夸他,原本徐音尘很有希望入阁拜相,兜兜转转,却闹到了如今的地步。
沈翊没下定论,只让吏部尚书先留着,过段时日再说。
他去找闻姝,又从闻姝那听来的别的闲话。
“徐音尘的续弦有喜了,我听旁的夫人在议论,说徐夫人近些日子兴高采烈的,年轻了好几岁。”这么多夫人贵女都在灵棚,说点闲话是难免的,闻姝一进去就有人和她说冷宫走水一事。
沈翊把热茶递给闻姝,“徐夫人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徐音尘预备辞官。”
闻姝捧着茶微怔:“为何?”
沈翊简单说了缘由,闻姝摇头,“这是场面话,徐夫人知道还不得气死,哪里能安养晚年。”
“嗯,过几日我寻他问问。”但其实不问,沈翊也能猜到,左不过是因为家里的事。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念得清楚,终有结束的一日,念不清楚,那就是一生的沼泽,无法逃离。
为难
顺安帝丧仪还未结束,百官中,便由尚弘起了头,恭请太子沈翊登基,以稳固江山百姓。
顺安帝拢共就三个皇子,如今独独留下沈翊,又早早册为了太子,登基实是众望所归。
但沈翊对此并未回应,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就这般拖着。
不过三日,百官便坐不住了。
先帝已去,太子迟迟不登基,这是何意?
有官员思忖着,“我听说太子因着荣郡王一事与先帝生了嫌隙,莫不是太子不愿登基?”
“这怎么能行?先帝只三个皇子,只剩下了太子殿下,他若不登基,我大周朝该如何是好?”官员忧心忡忡。
“正是,如今边境楚国虎视眈眈,太子殿下能平安从楚国摄政王手中夺得生机,可见是能带领大周走向更好的局面。”
“太子殿下文武双全,仁爱百姓,清明豁达,实乃帝王之选,左相可知太子殿下是何心意?”
众人皆看着尚弘,承恩公去后,尚弘这个右相就成了左相,是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首,盼着他拿个主意出来。
尚弘不紧不慢地捋了捋自己花白的长须,“递上去的折子没个动静,也不知殿下是如何打算的。”
百官面面相觑,当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不如左相再去求见殿下,转达百官心意,帝位长期空缺,只怕边境要动荡啊,如今永平侯又不在边境,楚国摄政王一旦出兵,这可如何是好!”官员颓唐不安。
谁都知道新旧交替之时最易动摇民心军心,二十年前的洛河之战就发生在先帝登基之初,虽然此时楚国还未有动静,只忧心是在蓄势待发,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