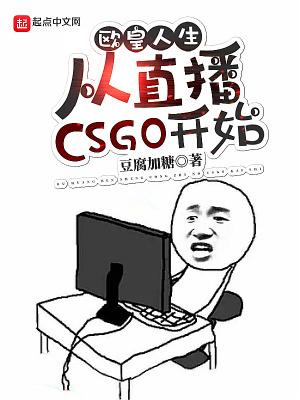极品中文>本座是个反派 剧透 > 第92章(第1页)
第92章(第1页)
康老大夫道:“不同环境、不同种类的毒虫,药性也不同,若是药性更强,或许不需要那么久的年份。”
江秋洵听后松了一口气。这句话听起来让药方靠谱了许多。
她转头看向林婵。
林婵闭着眼睛,脑门、脖子周围插着许多银针。
普通大夫做针灸,针眼处会溢出一点血迹,但林婵被下针的孔眼处没有一点鲜血,可见下针之人的水准。
待一刻钟后,所有银针取下,江秋洵看着仍闭目的林婵,问康白道:“康兄,她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
康白道:“可以的。”
江秋洵于是看向林婵,慢慢凑近。
林婵“听”到了江秋洵靠近自己的呼吸声,也感觉到了灼灼目光的靠近。
“阿婵。”江秋洵的脸上渐渐浮上微笑,说,“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
林婵:“……”
这人刚才好奇熏香的香炉摆件,在巴掌大的小铜炉前凑近看了半天,身上也沾染了浓郁的桃花香气。此刻她如此之近,不到半尺距离,林婵只觉被香甜的桃花香气包围,透不过气来。
江秋洵道:“你几天前就能看见了?你都没有告诉我,是不是为了悄悄偷看我?”
林婵:“……不是。”
林婵平日里出口成章,又善于揣摩对方心态,越是多想的人在她面前越容易受误导。而思虑较少的人也容易被她引导思绪。唯有江秋洵,胆大心细,性情执着,时常用赤诚与倾慕将她逼得退无可退。
或许正因为林婵一步三思,思虑过多,才会对率真如太阳一样耀眼的江秋洵没有半分抵抗力。
看看此刻的江秋洵,她如同一个逼问良家女子的恶少,笑得露出森白的牙齿,道:“那是为什么瞒我?身为未婚妻,却不是第一时间知道你伤情的人,人家好伤心啊……”
林婵:“……”
一旁被迫听着的康白忍不住想:这满脸的笑容哪里有一丝伤心了?
江秋洵发现林婵紧张得屏住了呼吸,忽然想到,在人前淡然镇定的林婵,不会想让属下看见她的窘迫。
哪怕只是打情骂俏。
于是江秋洵用余光扫了一眼康白。
她脸上的笑分明还很灿烂,这一眼却格外锋利,让康白打了个寒颤。康白连忙向林婵请辞,拖着满脸不高兴的老爹离开了林宅。
二人到了宅子外,康白还是没有放开康仁杏的袖子,康仁杏被他拉得差点绊了一跤,他连忙扶住:“爹,你小心。”
刚满七十岁的康仁杏一把甩掉康白的手,怒道:“不孝子,你想让你爹我享年七十岁?”
康白连忙陪笑认错。
康仁杏哼了一声,甩袖便走。他吃的盐比这混账玩意儿吃的饭还多,他能不知道避嫌?不拉他,他也会走。他担心姓江的居心不良,最多不给她好脸色,不会没眼色的杵着碍眼。
然而他还是不高兴。这个妖女果然不要脸,青天白日的……都是她把他们家主上给带坏了!
当夜禁宵前,宋翼带人去城南当街拿人,从赌坊抓走了净街虎等三人,直接关进了大牢的最深处。锦城经历多次战争,大牢不但房间多且坚固,还有专门关押重犯的水牢。
净街虎三兄弟便被直接下了水牢。
水牢中的牢房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把人关在半人多高的水中,算得上是“水刑”的一种。另一种只是地面潮湿。
水刑的牢房,因地势较低,污水沉积难排,不知存了多少年,又脏又臭,蛆虫遍生,各种寄生虫、细菌滋生。人关在里面,恶臭难闻,不能坐下,只能站立,要不了多久,就会身体浮肿,肤肉糜烂。等到疲惫到极点的时候,便倒入污水淹死。
净街虎等人被关押的是另一种。这部分牢房地势略高,被肮脏的地下水包围,阴暗潮湿。灰黑色的霉菌爬满了湿漉漉的墙壁,石缝处还残留着些许青黑色的青苔。
李拓等人在江湖上混迹多年,不需解说,一眼看见旁边的水刑牢房便明白了其可怕之处。
被晏寒飞一脚踹在下腹的男子脸色煞白,道:“大兄,这,这是传说中锦城关押细作的水牢房啊!”
这个多年以前专门关押敌方细作的地方,老狱卒都不愿意来,就连焦知县都不曾听闻,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但倒回二十年前,那时候它还是许多本地人小时候被长辈恐吓的工具,可止小儿夜哭。
却不知这位新来的宋县尉是如何在抵达县城的几日内知道水牢的存在,还把它找了出来。
……
“宋大人这几年因被九皇子的人压着不能出头,明着是在京兆伊做捕头,暗中却是在为刑部办事,奔波各路,捉拿要犯、刑讯审问都不在话下。他到锦城县后,先以县尉之职接手了兵权,又拉拢了积年老吏。任期已经快满的焦知县贪婪傲慢,衙门里无权无势的底层小吏被他和上任知县欺压盘剥已久,正好为宋县尉所用。”
第二日,早膳后,昭节来林宅向师父和未来师娘汇报了昨夜抓捕净街虎三人的结果。
江秋洵听完后,担心道:“那李拓和金家关系不浅,金家又是焦知县敛财的爪牙,万一被焦知县放了……”
林昭节便告诉她,三人关押在水牢,就算被焦知县放出来也没事儿。锦城县谁不知道,进过水牢后遗症多得很,别说水刑,就单单因为恐惧而造成人犯的不举、头疼、抽搐……的人都数不胜数。
之后李拓等人就算发觉了身体的异常也只会以为是这一次进水牢造成,不会怀疑是晏寒飞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