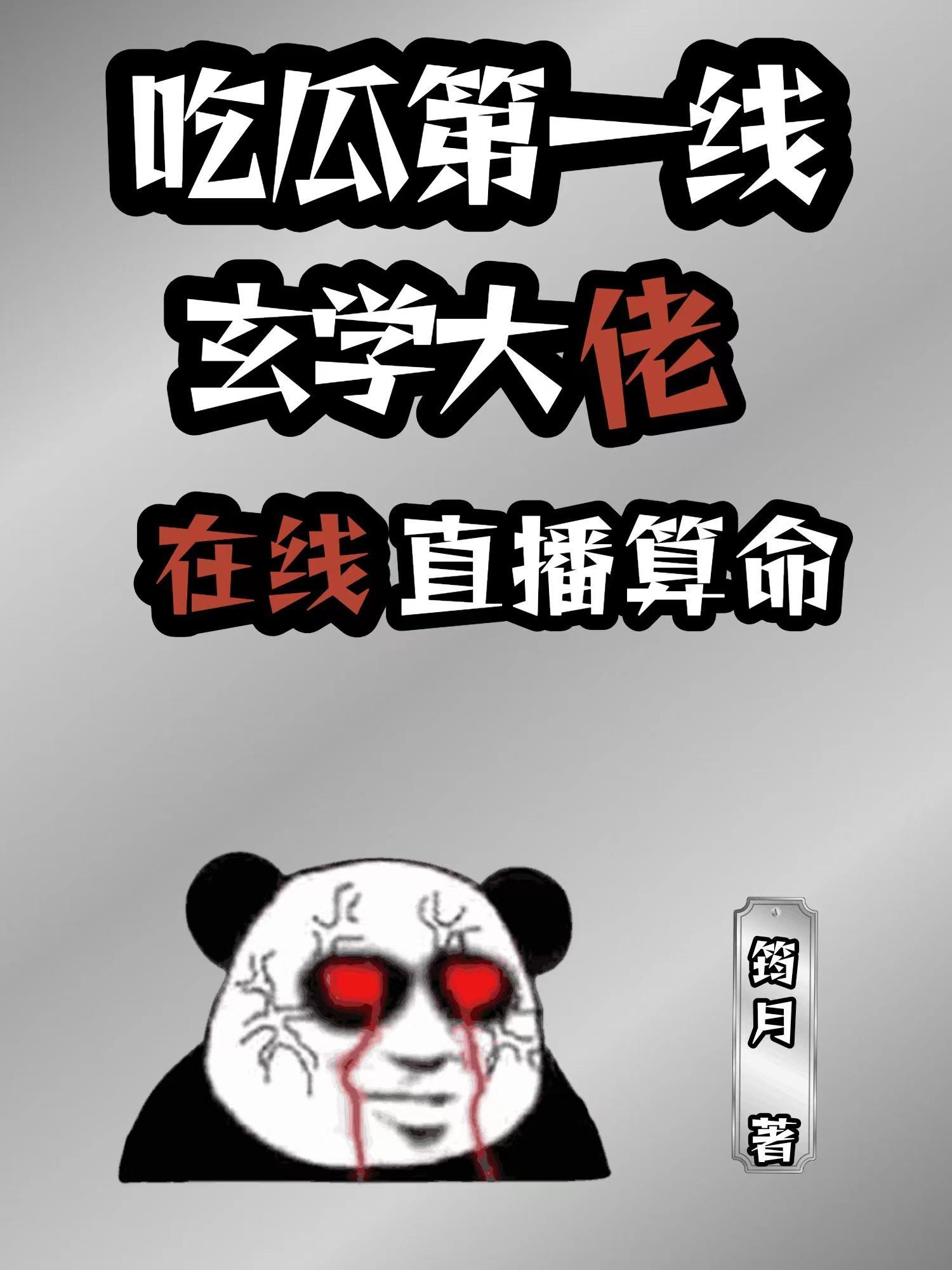极品中文>种田文男主拿错反派剧本 百度 > 魔头养成第二十五式(第1页)
魔头养成第二十五式(第1页)
离之前那林中插曲已过去几日,霍且非仍旧不见踪影。韶言和曾暮寒已经沦落到出门挖野菜的地步,但也坚持不了太久。
转机自四月十一开始。
先是韶言从门口捡到一排被咬死的野物。尽管摆放的整齐,韶言开门的时候还是吓一跳。
野兔脖子被咬穿,留下两个血窟窿。似乎是狼,可韶言很难不联想到之前见过的狐狸。
这是什么意思,警告?
这些畜牲通人性,可能是猜到恒水居的粮食快见底,所以才送上食物。
可畜牲到底是畜牲,韶言盯着野物脖颈上的已经干涸的血液,心想:它们咬过的东西真的能吃吗?
毒死还是饿死,这可是个问题。韶言叹口气,心想还是别让师兄看到这副场景。
他伸手拽住离他最近的那只野兔的两只耳朵,准备好好收拾一下,结果从那死物黑色的皮毛里看到格格不入的一片白。
是一张纸条,已被血染红了大半,但上面的字迹仍清晰可见:放心吃,毒不死你。
如此娟秀……这绝非是霍且非的字迹。但韶言看到这几个字,却莫名其妙觉得熟悉。让他忍不住想到先前在林中见到的那名红衣男子。
纸条里裹着一片银色的柳叶,在阳光下几乎晃到韶言的眼睛。他伸手去拿,险些划伤自己的手。
竟是一把巴掌大的匕首。
那纸条已失了用处,原本随意处置便好。可韶言鬼使神差地
将它团成一团塞进袖子里。
他总觉得这其中有一些他未知的谜底,而这张纸条或许是解谜的关键。至于那匕首,虽然小了些,但着实锋利,倒方便韶言剥兔子皮。
曾暮寒忙着收拾后园,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正好给了韶言收拾门口的时间。
待他洗净门前和自己手上的血污,太阳已升起老高。韶言眯起眼睛盯着林中斑驳的树影,呆呆的不知在想什么,也可能什么都没想。
他坐了有一会儿,鬓间的汗水滴到衣领里才回过神,拎着一只肥兔子就去了厨房。曾暮寒进来的时候闻到一屋子肉香,他愣了片刻,问韶言:
“莫不是我鼻子出了问题?野菜还能煮出肉味?”
韶言正忙着给灶里添柴,听他这话忍不住笑,灶灰蹭了一脸:
“师兄鼻子好着呢,当真是肉。”
他寻思了一下,还是莫要告诉师兄这肉的来历。他也不知为何要瞒着师兄,只是隐约觉得这事师兄还是不知道最好。
因此他又补充一句,“桂花糕和云片糕送来的,看来师父还没忘记咱俩。”
也不知道曾暮寒信还是没信,反正他没多问。十几只兔子吃了将近半个月,许久未见的桂花糕才回来,脚上系着一个茄袋。
“咕、咕咕。”
曾暮寒翻遍了厨房,连霍且非压箱底的点心盒子也没放过,可惜一块点心也没找到,只剩下一堆碎屑。
他没办法,只好捧着这些边角料领着
韶言给桂花糕鞠躬道歉:
“对不起啦,只剩下这些了。”
桂花糕并是不不讲道理的雪鸮,伸出翅膀在韶言和曾暮寒的头上拍了两下表示谅解。
它刚飞回原位,云片糕贱兮兮地从它身后探出脑袋,对着曾暮寒手里的点心渣子蠢蠢欲动。桂花糕瞪它一眼,一口叨在它头上。
“咕!咕咕咕咕!”云片糕惨叫。在它们战场的远处,一只淡黄色的猫头鹰慢慢地飞进来,韶言似乎从它的圆脸上看出无语的情绪来。
一直跑长途的马蹄糕居然回来了,这预示着霍且非很有可能遇见大麻烦。马蹄糕喝了水,飞到韶言的肩膀上,示意他把纸条拿下来。
那纸条上的字尽管十分潦草,但确实是霍且非的字迹。
纸条上并没有交代霍且非的现状,事实上霍且非对自己只字未提。
那上面只是模糊地说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让桂花糕送回些银两,并语重心长地说韶言年纪不算小了,可以自己下山。
韶言心想恒水居也不是没有银钱,怎么还要让桂花糕跑一趟。他打开轻飘飘的茄袋,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是十几片金叶子。
他和曾暮寒对视一眼,从彼此的眼神里都看出了不理解。韶言心想师兄大概不会放心让他独自一人下山,原本打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但曾暮寒远比他想象的开明得多:
“让桂花糕它们跟你一起去,买的东西一多,你自己肯定拿不回来。别
耽误太久,三天以内一定要回来,记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