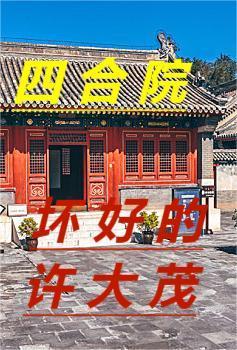极品中文>万人嫌小聋子嫁给渣攻舅舅后全文阅读 > 第20章(第3页)
第20章(第3页)
“您能弹一次给我听吗?……在我能听见的时候。”
盛愿轻轻阖眼,想象先生坐在钢琴前演奏的情景,似乎看到了他指节修长、骨感分明的手指在黑白色琴键上跃动。
如此一来,他或许便能心安理得的在那副未完成的油画上点上一粒红痣。
沉默替换了男人的回答,他的视线从陷入黑甜梦乡的人脸上离开,移落回纸上。
被划去的,无须在意。
牧霄夺绕到岛台前,沉沉俯身,蓬乱的丝擦过他的下颌。
他一手垫在盛愿的腿窝,另一手搂着背,把没什么分量的人轻易打横抱进怀里。
黑夜令感官和触碰变得无比清晰。
起初他不在意,直至感受到那颗年轻的心脏在自己怀中有力的跳动,他才蓦地觉这个年轻人的鲜活与自己身上腐朽的铜臭气是多么格格不入。
他把盛愿放在床上,不经意一瞥,目光掠过那几瓶还没来得及收起的药瓶。
他眸光沉沉,在床边站定片刻,而后压低脚步声离开。
晨曦展露,他们零零碎碎的短暂交集伴随着夜色一同消散。
第17章
那夜之后,好像二人的缘便就此尽了。
他们依然没有互相的联系方式,相逢不靠约定,全凭巧遇。
零零散散的交集依然有,左右不过那一两句。
譬如那些带着露水的清晨,盛愿礼貌的唤一声“舅舅好”,先生会报以浅笑,而后踏出庄园。
他目送他驾车离开,再见面或许是晚上,亦或者是次日清晨。
先生经常会出差,有时,在盛愿毫无觉的时候,便与他相隔了一整个大洋。
先生不在的时间,盛愿便一如既往的配音和画画,或是独自漫步在偌大的庄园,像误闯仙境的爱丽丝。
大多数时候,他会把画架搬到室外,立在花园前的鹅卵石小路上,画鸢尾、绣球、铃兰……
园丁见小少爷时常来光顾,一坐就是半天,不甚熟练和他比划手语:“总画那些花,不腻吗?”
盛愿笑道:“不会腻的,一日不见,你种的花就千变万化,我可不能错过。”
园丁日日与花作伴,不懂什么是千变万化。只觉得,那应该是夸奖。
某日,园丁指着花园里一处新开垦的良田,问他:“您觉得在这里种什么好?”
盛愿停下手中画笔,不假思索:“玫瑰。”
至于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
次日,园丁早早去了花圃,抱回一捧新鲜的玫瑰花苗,站在花园里等他。
他说,那片田是先生留给小少爷的。
盛愿从未拥有过这么大一片可以种花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