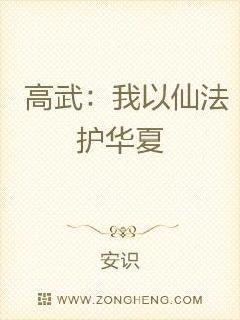极品中文>剑指云天 > 第3章 入关(第2页)
第3章 入关(第2页)
“放心,看我的!”洪四叔说完,右手大拇指与食指,指尖轻捏,放入口中,口中吹动间,数声口哨声,突然响起。
谷鱼与梁钟,以及十数名燕国人,惊奇现,数十匹战马,疑惑片刻,便乖乖走向面貌狰狞的洪四叔。
那些战马很是亲切般,自动伸出舌头,去舔洪四叔右手,洪四叔伸手,一一抚摸它们,像是老友重逢一般。
“您还有多少绝活,没教我啊?”谷鱼惊奇间,开玩笑询问洪四叔。
“不当兵打仗,本以为用不上,所以未教你,有些生疏。”洪四叔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解释道。
“洪四叔当过兵?”梁钟好奇开口问道。
“年轻时,当过几年兵,先不说这个,分好战马,赶紧离开此地!”洪四叔答完梁钟,连忙转移话题,催促众人赶紧离开。
众人安排妥当,死去燕国人,以及北晋骑兵尸体,短时间内无法掩埋,众人快搬运尸体,各堆积于一起,捡些木材一起点燃焚烧,算是清理尸体。
谷鱼骑马,带着那名所救少妇与幼儿,洪四叔带着一位老人,梁钟带着一位老妇人。
其他会骑马之人,各自带着不会骑马之人,沿着官道,向燕国边关,急而去,连那些空马,皆被洪四叔带走。
众人离去一个多时辰,一队上千人以上,北晋国重甲铁骑,便是一路烟尘,奔至官道打斗处,焚尸现场。
有士兵下马,探查一番之后,向铁骑将领,禀明情况。
铁骑将领挥手之间,那名士兵上马,上千重甲铁骑,整齐划一,疾追向谷鱼等人,所去方向,地面震动不已,地上尘土飞扬。
日落时分,晚霞满天,谷鱼等人,已见远方牧边城,众人方才露出喜色,各自松口大气,却仍是马不停蹄,向牧边城方向而去。
天色渐黑之时,众人方至牧边城,东城门之下,牧边城依山谷而建,两边皆是悬崖高山,山脊有城墙连绵不断,是为防守外敌而建。
此时有人下马,上前叫门,牧边城上,火把早已点起,城楼之上,站着许多将士,正打量下方,依稀可见十数人,借着火把,正确认城下那些人身份。
“各位军爷,我们是燕国人,麻烦开门,放我们进去!”一名燕国男人,扯开嗓子喊道。
“你们怎么证明是燕国人,可有身份路引等证明?”上面一位军士,大声喊话问道。
城下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却无一人,拿出身份路引等证明,又有数人抬头,喊话城楼之上,那些将士,叽叽喳喳,嚷嚷声不停。
“没有路引,或其他身份证明,无法开城门,放你们进入,若有北晋奸细混入,我们没法向上面交代!”城楼之上,一名将士,向下方众人,大声喊话道,仍未有开城门之意。
谷鱼救下的那名壮汉,指着谷鱼与洪四叔,突然喊叫道:“几个时辰前,我们刚被北晋骑兵追杀,要不是他们,及时出手相救,我们早已死在关外,这些马匹,便是北晋骑兵战马,战马可以为证!”
城楼之上将士,又仔细向下观望片刻,几人又商议一阵,之前那位将士,仍然喊道:“不是我们,不想给你们开城门,上面刚刚下达军令,必须出示路引,或其它身份证明,方可开城门,抱歉了!”
话音刚落,突然地面震动,城楼之上将士,城门之下众人,向远处望去,只见远处,上千火把,照明的重甲骑兵,正整齐划一,向牧边城方向,疾驶而来。
城门之下,众人开始慌乱,又开始着急喊叫,让开城门,城楼之上将士,也不知该不该开城门,双方就此僵持,远处重甲骑兵,却越来越近。
众人正无计可施间,谷鱼右侧,马背上的梁钟,叹息一声,右手从怀中,取出一块黑色令牌,举过头顶。
对城楼之上将士们,大声说道:“天监司梁钟在此,请开启城门,有军机大事密报!”
洪四叔突然听见梁钟,道出天监司之名,当场一惊,瞬间又镇定自若,黑夜之中,无人现,洪四叔脸部抽动瞬间,有些异样。
城楼之上,那些将士们一听,同样一惊,数息时间,城上一名将军,不敢怠慢,大喊一声:“开启城门!”
城门很快开启,城下众人,骑马快入城,城门又很快关闭。
此时千骑重甲骑兵,片刻之间,已至城门之下,整齐划一,勒住缰绳,人马合一,突然毫无声息停下,没有一匹战马,出一丝声音。
“请交出,刚入城的北晋重犯,我乃北晋国,黑骑部!”千骑重甲骑兵中,有一兵士,对着城楼之上,大声喊道。
城楼之上,众将士一听,北晋国黑骑部,皆是倒吸一口凉气,吓了一跳,北晋国重甲骑兵,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曾千里奔袭,剌杀燕国镇国大元帅,虽被燕国铁骑包围,损失惨重,刺杀并未成功,但重创燕国元帅精锐护卫,最终仍是带着重甲骑兵尸体,井然有序退走。
城楼之上,将士们虽是一惊,但仍是不卑不亢,理直气壮。
城楼上那名将军,大声指责道:“入城之人,皆是我燕国子民,你们无故追杀燕国子民,是为何意,想与我燕国,开战吗?”
城楼之上,众将士们,齐齐大喊一声:“杀!”
上千重甲骑兵,也是无奈,燕国将士,素来霸道无比,加上险关要塞,不是千人重甲骑兵,便能攻陷之处。
人已入城,重甲骑兵们,虽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又不能与燕国,立即开战。
重甲骑兵,又喊叫片刻无果,只好整齐划一,转身撤退,向黑暗之处,奔驰而去。
城楼之上,众将士们,见重甲骑兵,仍是井然有序离去,方才松口大气,有些将士,抬手擦擦额头冷汗,看向远去火把下重甲骑军,不得不暗自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