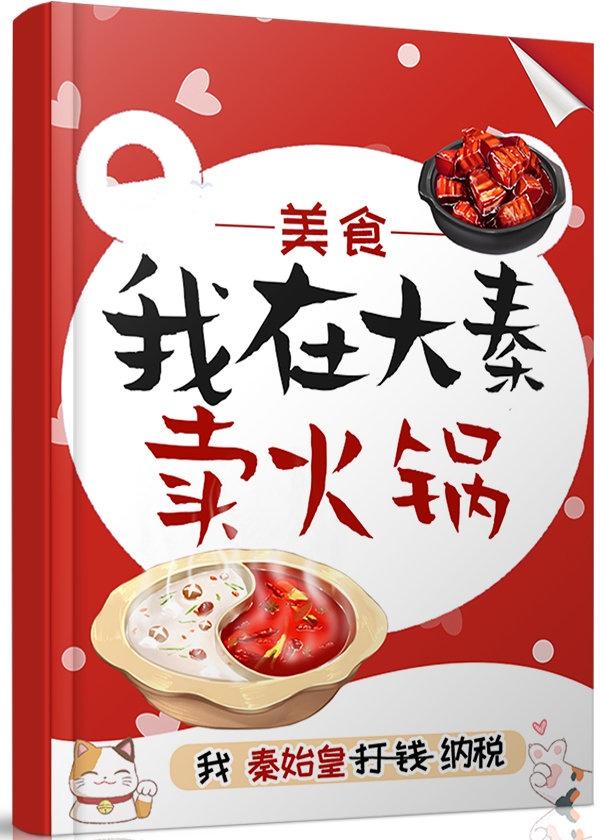极品中文>驸马又纳了一个妾 > 第126章 惊梦(第2页)
第126章 惊梦(第2页)
可时间从未这般漫长过,没有人是他的随从,哪怕是千牛卫,可千牛卫也并非他的死士。
他曾经为元煊被废之后东宫无一人为他说话而暗自庆幸甚至喜悦过。
也许从前那些对元煊的赞美也不过是为了自表功绩而已。
直到最后一刻,崔耀给了他一个台阶,一个,让元煊向上的台阶。
他不明白,分明自己才是天子。
人人口中说着忠孝之语,可究竟效忠的是谁?
元嶷看不分明,他不明白,不甘心,却又像年幼时一样,根本拿不动那把宝剑。
元煊曾经在金墉城待过一年,元嶷不知道究竟谁是元煊的人,或许都是。
宫人低低询问交谈的声音传来。
“皇上又夜惊哭笑了?”
“皇上疯了好些天了。”
“听说当年清河王被囚,也有人传她疯了,看来被关久了,就是真龙天子也会疯嘛。”
“什么真龙天子,也不过与我们凡夫俗子一般都是人罢了,人都有生老病死,自然也是会疯的。”
元嶷终于痛哭起来,在暗夜里,在无尽的莫测中,想要回到最初最安全的地方。
可这世上哪有最安全的地方。
“我给皇上端安神汤来,叫皇上喝了好生安歇吧。”
一道声音低低响起。
“这么费劲讨好做什么?”
“这些时日他一有风吹草动就大喊有人要害他,连累我们几多波折,叫他安静下来免得我们宫人也难安寝。”
暗色的身影缓缓走入内室,到了床榻之前。
“陛下,陛下……”
元嶷不肯转过身,甚至往床榻里缩了缩。
他日夜穿着自己唯一的一个软甲,这软甲也并不甚软,甚至硌得他生疼,生怕有人会突然暴起,抽出一把刀剑来。
那暗影却俯身遮住了元嶷为数不多能感知到的光。
“陛下,梁郡公的精兵,已至城外了。”
元嶷心中大喜,一咕噜坐起来,惊疑不定看向了眼前的人。
似乎有些陌生,又似乎有些眼熟。
“陛下,我是长乐王殿下的家仆啊,您忘了吗?”
元嶷这才慢慢松懈下来,又连忙倾身将人拉住,“明达带着綦家的精骑来了?!就在城外?那他人呢!”
“殿下也惦记着您呐,我听宫人说殿下您惊梦不安,特地熬了汤药,您安歇一晚,明天天一亮,就是您的大日子啦。”
元嶷狐疑地看着他端着的汤药,“既闻此喜讯,我病自愈,何须安神。”
那宫人笑了笑,“明日是一场硬仗,若陛下惊喜过度,一夜未眠,明日可就没劲儿啦。”
元嶷渐渐起了疑心,“你在我面前试药我便喝。”
黑夜里头,帷帐被掀起一半,宫人背着光,叫元嶷看不分明,只能瞧见在黑暗里还亮着的眼眸。
他倏然心头一紧,生出格外的恐慌来。
宫人抬手,似乎要取东西试药,下一瞬间,一只铁手死死抓住了元嶷。
元嶷挣扎了起来,他想要高声呼叫,“来人!来人!有刺客!有刺客!”
但没有人来。
这些时日元嶷喊过太多次了,但凡有陌生宫人近身侍候,他都会惊呼刺客,要千牛卫拖下去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