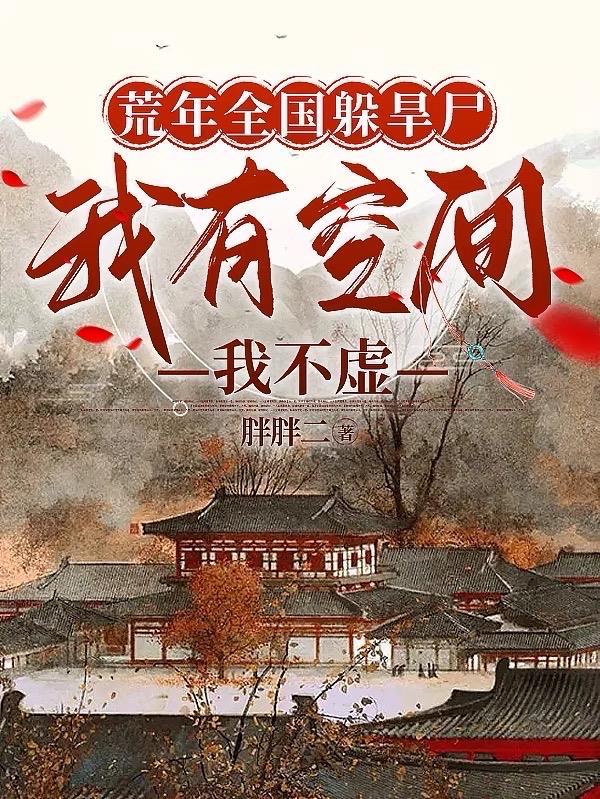极品中文>慢慢是啥歌 > 第6章(第3页)
第6章(第3页)
“你吃吗?”荆平野拆开包装。
应逐星张了张嘴,正想拒绝,一粒糖毫无防备地喂进了嘴里,掌心短则接触到他的嘴唇。强烈的酸在口腔里炸开,应逐星猛地咳了声,吐出了糖粒:“你……”
“怎么给吐了?”荆平野抱着恶作剧的心态,忍着笑,“很好吃的。”
应逐星酸得皱眉,却说:“挺好的,是我有点吃不惯。”
没有脾气,倒是与幼时很相像。以前他和应逐星的相处模式就是这样,荆平野负责出格、捉弄和玩笑,而应逐星负责点头、崇拜和宽容,无论怎样,应逐星很少生他的气。
不过现在可能只是不够熟络,碍于面子没有作。
思及此,荆平野心情变得有点坏,他吃了一颗糖,说:“回去吧。”
病房里。
外头刺眼的金色阳光透射进来,如同海绵吸走其余色彩,亮得惊人。徐瑶犹疑地看着夏蕾:“真的只要1oo?昨天我转过来,就觉得一定很贵,护士态度那么好,连厕所都干干净净的。”
夏蕾面不改色:“这有什么假的?现在医院这么多,想留住人,总得下点本,哪能跟咱们那个时候一样脏乱差。”
徐瑶神情动摇,却还是说:“还是在家里好,1oo也是钱。”
“你现在回家住,逐星还得分心照顾你,等开学了,万一再出个岔子,他能安心学习吗,”夏蕾拍了拍她的手背,“你是不是不放心逐星一个人在家?”
徐瑶眼眶泛红,喉咙挤出干涩的声响。
“如果你不嫌弃,我把逐星接到家里来。”
话音未落,徐瑶有点惶然道:“这太麻烦你——”
“这有什么麻烦?逐星比平野乖多了,不闹腾,总归只是吃饭多一双筷子的事,他和平野一起,彼此也有个伴。再说,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夏蕾说,“这事我来跟逐星说,你就好好养病,以后说不定能看到逐星上大学。”
或许是夏蕾最后一句话所描述的蓝图过于理想化,徐瑶神情动摇,没有再推拒,只是死死攥住夏蕾的手,重复说“谢谢你”。
从小卖部回到四楼时,荆平野遥遥看见坐在门外银白色长椅上的夏蕾。她抬眼,招了招手,对应逐星说:“来,坐这儿。”
应逐星坐到了夏蕾身旁的空位,而荆平野坐在了他旁边。
“你妈妈问我费用了,”夏蕾道,“我说不贵。”
应逐星松了口气:“谢谢您。”
“那说说吧,为什么要把你妈转到这儿来?”
荆平野同样看向应逐星。他微微低着头,手指扣弄着盲杖,沉默了半分钟后,他问:“我妈妈睡着了吗?”
“睡了,”夏蕾说,“你说就行。”
应逐星点点头,轻声道:“因为我打算放弃治疗。”
口腔里糖果的酸壳已经溶解,过于盛大的甜腻漫延开,荆平野怔怔地看向应逐星,眼睛睁大,应逐星声音平静:“医生说了,我妈的生存期只有一两个月,无论是化疗、放疗还是其他介入治疗,都只会让她很痛苦,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最后最后过点舒服的日子,至少麻醉药物会减少痛苦。利群是滨城唯一一家有临终关怀的医院,所以我办了转院。”
夏蕾沉默许久,才说:“你倒是很果断。”
应逐星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然而荆平野却无法忽视应逐星有点抖的手指——只有他现了应逐星尚未成熟的证据。之后两人谈论了什么,荆平野心不在焉的,并没有听进去,再度回过神时他们已经离开医院,坐在回家的车上。
车窗玻璃半落,荆平野看见外面百货大楼上偌大的手表广告,四周彩灯点缀,成为城市里最为普通的人造彩虹。
每个人都习以为常,因而没有驻足。
但应逐星看不见,荆平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