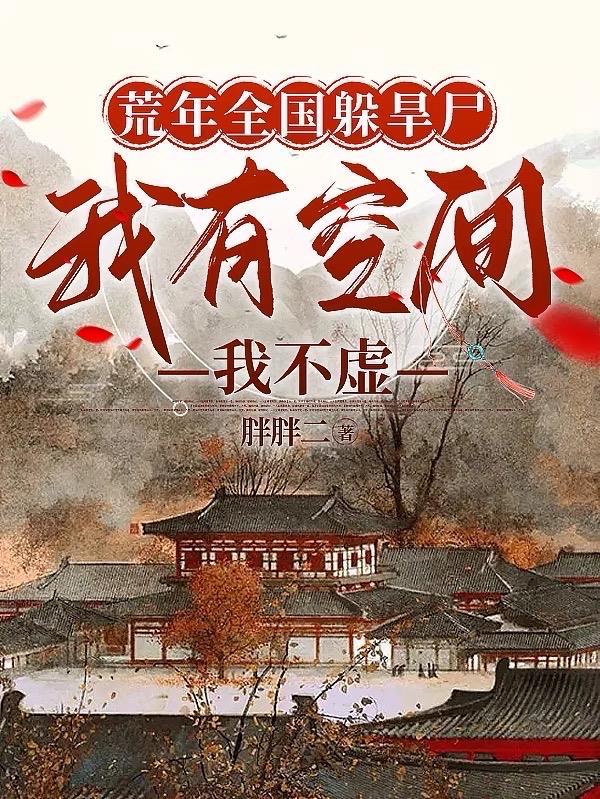极品中文>2020新婚姻法第三者的处理 > 第72章(第1页)
第72章(第1页)
蒋纯先是一愣,紧接着是对自己朋友的怀疑,但又很快被他说服。最后关于这个观点的疑问都抛在脑后,再也没试图剥丝抽茧过。
只是那位教授说过的这句话,始终让他记忆深刻,犹是昨日。
现如今,在距离那一场讲座已时隔不知几年后,蒋纯面对从天而降的秘辛馅饼时,却恍恍惚惚地再一次想起那位教授的观点,终于认为他不单单只是在故作高深,还掺有一定的事实道理。
蒋纯想不通。他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被他知道,他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一口馅饼竟然锤到这么死,叫他都找不到任何可以替代的解释维护他亲亲表哥岌岌可危的幸福。
——是的,这个突然而至的秘辛,事关他那位只大他一代沟的、他敬爱的表哥。
他放空着脸,等了许久直到没有声音,才从洗手间的隔间里飘出来。却没想到才晕晕乎乎,好像脚下踩着云朵还没走几步,一转弯就看见他的嫂子、他表哥的合法伴侣垂着头在洗手池中洗手,不知等了他多久。
于玚还是那个装扮,一成不变的白衬衫,和卡其色休闲长裤。
弯曲的细长银色水龙头下,细细的水流和着潺潺的静谧水声,亲吻着他的手指,在橙色灯光下吹奏出稀里哗啦的进行曲。
蒋纯黑葡萄似的眼睛,茫茫然着终于从云端落下,坠落在这个男人的肩头,看他镇定自若地洗着手。
“你都听到了。”于玚开口,镜子里他的脸因为低垂的角度看不清晰情绪。直到青年收回手,从口袋里抽出叠得整齐的手帕来,才完整地露出一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你听到了多少?”
蒋纯呐呐着,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下一瞬间,才如梦初醒似的,发出一声急促的喘息,视线对上镜子里于玚的眼,不知说什么。
于玚垂着手,看着镜子里的年轻男孩儿,他记得他,也知道他。
青年脸上镶嵌的玫瑰一样的嘴唇勾了勾,笑了一下,温和漫上他的眼瞳,淹没成海。于玚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一般,看上去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放松之感。
他转过身,对晏冷淡的表弟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姿态礼貌而克制:“跟我来吧,洗手间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蒋纯的眼神从他的脸上转到他的手上,反应却是往后退了两步。
“不,我不能。”蒋纯咽了咽唾液,天然的直觉疯狂地提醒着他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他对于玚说:“你和表哥的事,我不能掺合。”
话一旦开了头,就没那么不知所措。
他定了定神,深吸一口气,告诉眼前被他听到秘密的青年自己的立场:“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应该对表哥说的,都不是我。”
“哪怕是对不起他的错事吗?”
于玚那张显得他分外年龄小的娃娃脸上是平静的,一双好似会说话的眼睛看了他一眼,似乎对他的反应早有预料,并没有流露出多少惊讶的意思。
但是他说出口的话,却无疑在映射着蒋纯、他刚刚听到的那些话都是事实。
“对,没错。”蒋纯忽然镇定了下来,说:“你是我的嫂子,我相信你比我更要了解我的表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无论你做了什么错事,都需要你去亲口对他说,而不是通过我来替你转达。”
“你不想知道?”于玚转过脸,语气奇怪地问他。
“不,我不想。”蒋纯说,“这不是我该知道的事。”
于玚勾了勾嘴角,他点点头,忽然又问:“你已经听到了,不好奇?”
蒋纯的反应更理智,也更直接,他盯着于玚说:“你说的对,不该知道的我已经听见了。但是有关两个人的事,任何人都不应该去插手,我也没资格去探听。”
说完,他就好像是有了很多力气一样,跟于玚说了一句“再见、嫂子”,还来不及听青年的反应,就逃也似的脚底抹油跑了。
德国华裔,蒋家蒋纯,今年二十四岁,偶然出行,于商场洗手间面临了短短前半生以来最大的临时磨练,知道了他二十四岁以来听过的最大的秘密,且没有之一。
在于玚面前溜得飞快的蒋纯一屁股坐进沿途经过的某个包厢里,脱力般失去控制管理,靠在柔软的椅背前。
他在侍者甜美的微笑下顺着菜单推荐,浑浑噩噩点完了东西,半点没往心里去。
直到侍者离去后半晌,蒋纯才从呆呆的状态里回过神,回想起于玚在洗手间压低的声音,双手一下子捂住脸,拄在桌面上发出压抑的嚎叫。
我屮我屮我屮我屮我屮我屮我屮我屮——!!
他心中的小人拼命地蹦来蹦去,张牙舞爪地抓狂尖叫,甚至还没有形象地在地面上滚来滚去,蹬着小腿儿宛如羊癫疯患者在犯病。
蒋纯简直都要泪流满面,想要给他哥跪了。
他喘着气,从指缝里睁开眼,欲哭无泪地想起刚刚在洗手间发生的事,于玚的声音不停地回响,包括他不小心偷听到的话。
——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从于玚眼皮子底下成功溜走的!
太刺激了,蒋纯想,他就没经历过这么刺激的事儿,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该不该跟她表哥说。
蒋纯的脑海里犹如出了问题的剧场投屏,他越拼命告诉自己不要去想不要去想,他的大脑越要一次又一次地回放。
他噫噫呜呜地咬着牙,小可怜一样丧眉拉眼,觉得那场面比他被他的亲亲表哥扔到军中暴打和高强度操|练都要更彷徨无助,难以应对,堪称是他人生中一大难题的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