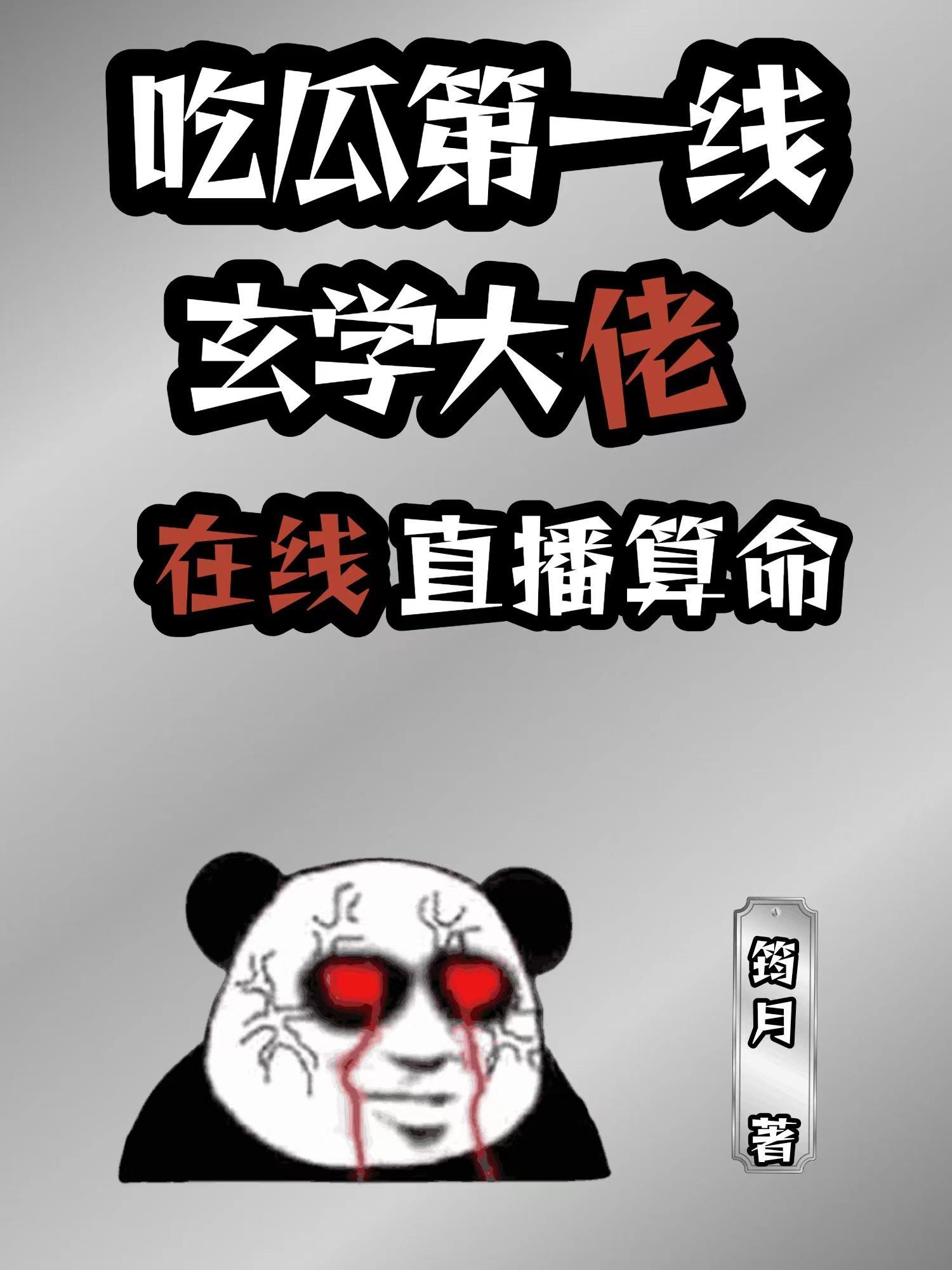极品中文>趁雪下夏诺多吉全文阅读 > 第14节(第2页)
第14节(第2页)
次日一早,杨皓月和钟笛作为社区代表去参加老丁的葬礼。老丁的儿媳见到钟笛,忙问老丁除了遗嘱之外,还有没有留其余的话。钟笛摇头,说都在遗嘱里了。
老丁的遗嘱平平整整地放在床头柜上。南陵市区及翡翠湖的三套房产留给儿子儿媳,退休存款及保险金留与妻子,社区家里的一只猫和一缸鱼托钟笛妥善处置。
杨皓月对钟笛说,以前大家都以为是老丁家暴,所以他老婆儿子才对他深恶痛绝,现在才知晓,亲人将他推远只是因为他这张嘴不好。
“所以说,利嘴比利刃更能伤人,人活着最该修炼好的就是嘴上的德行。”
钟笛心里弥漫自责和愧疚,对着老丁的遗像鞠躬时悲上心头,没忍住眼泪。她总以为她的管家工作做的比旁人细比旁人好,可她明明觉察出老丁的不对劲,却没将自己的直觉坚持到底,最终最大的疏漏出在她这里。
杨皓月安慰钟笛,说她已经做得很好了,让她别有心理负担。
又道:“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哭。”
钟笛在杨皓月心里是个怪人。
她私底下的性格给人一种闷、沉和无趣之感,和她外表上的先天优势形成极大的冲突感。她看上去并不热衷于跟他人建立亲密连接,也似乎没有人能真正走进她心里,可她能出于想把一份工作干好的目的,在工作场合放下她冷淡的面具,真情实感地为业主们服务,在不自知的薄情里流露出真实的柔软。
她缺钱,永远用最笨的办法去缓解窘迫。但要说她呆板,她又十分懂得抵御外来的诱惑。至少在杨皓月这里,从未听过她与任何异性的花边新闻。其实要是她想,她面前有的是捷径,她完全不必受这份罪吃这些苦。
她就像一个清晰掌握并接纳自己命运的渡劫人,对一切苦和乐都持有最平和的心态。她也好像比旁人更明白自己的宿命。
杨皓月在自己的这番评判里感到一丝悲凉,莫名想到红颜薄命这个词,特别是看见她掉眼泪的时候。
“回去之后记得探望一下525的业主,听说她情绪波动比较大。艺术家嘛,天生的敏感。这事跟她没关系,别影响了她继续搞艺术。”
“好。”
杨皓月觉得给钟笛增加些工作量,比安慰来得有用。
-
钟笛请工程部的师傅帮忙把老丁的鱼缸挪至服务台的会议室。余湘见状,问这些鱼能不能由她来养。
“您养过鱼吗?”钟笛问。
“可以学。”
“好。”钟笛觉得成全余湘的心意,能为她心底的歉意提供一个出口。
鱼安排妥当后,钟笛趁下班时间去寻老丁出事后消失的那只猫。她带着小猫最喜欢的毛球玩具,沿B区周围的绿化带和花圃轻声呼喊它的名字。
找了许久无果,她这才想起来去消控室调监控。她刚要骑电动车赶过去,凌程和一名安保提着一个猫笼从小花园里走出来。
“它是叫馒头,对吧?”凌程靠近后,问钟笛。
“是。”
安保对钟笛说:“可算找到了,你打算养在哪儿?”
钟笛还没想好。
待安保离开后,凌程说:“要不让我把它带回南陵,跟我家里的那几只养在一起吧。”
“你、你家养猫了?”
“嗯,我妈四处旅行之后,我爸觉得孤单,领养了三只流浪猫。”
钟笛的脑子里闪过一些昔日的片段,想起他曾经说他父母闹离婚的事,也不知如今两人是什么状态。
她问:“方便吗?”
“方便。”
就这样,老丁的猫也有了归宿。
“那这两天你怎么养?”钟笛问。
“麻烦你取一些猫砂和猫粮来,哦对了,还有它喜欢的玩具和零食罐头之类的,我看它情绪不太好。”
“好。”
找到需要的东西后,凌程一个人拿不下,钟笛抱着一部分东西跟他一起上楼。
余湘听见动静,邀请两人忙完之后去家里坐坐。片刻后,钟笛和凌程面对面坐在525的餐桌上。
“你们俩,是不是认识很久了?”余湘问这句话的时候,正在为二人分食她做的夜宵。她语气很淡,不像问句,更像是陈述句。
凌程的反应是看向钟笛。
钟笛认真剥一瓣橙子的皮,剥好后把果肉送进嘴里,“是,很小就认识了。”
凌程安然收回视线。
余湘放下餐勺,“谈过恋爱?”
“嗯。”仍是钟笛在回答。
余湘不再问,把两碗分配很均匀的汤羹各放一碗在钟笛和凌程的面前,“炖了四个小时,你们尝尝。”
电视里在播放一场音乐会。钟笛品尝食物的时候,余湘和凌程找到共同话题聊了起来。
这场面很熟悉。凌程是充满才情的男人,他丰富的知识面和敏感的艺术嗅觉总能为他吸引志同道合的朋友。
“小钟,你平时除了工作,都干些什么?”余湘担心冷落了钟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