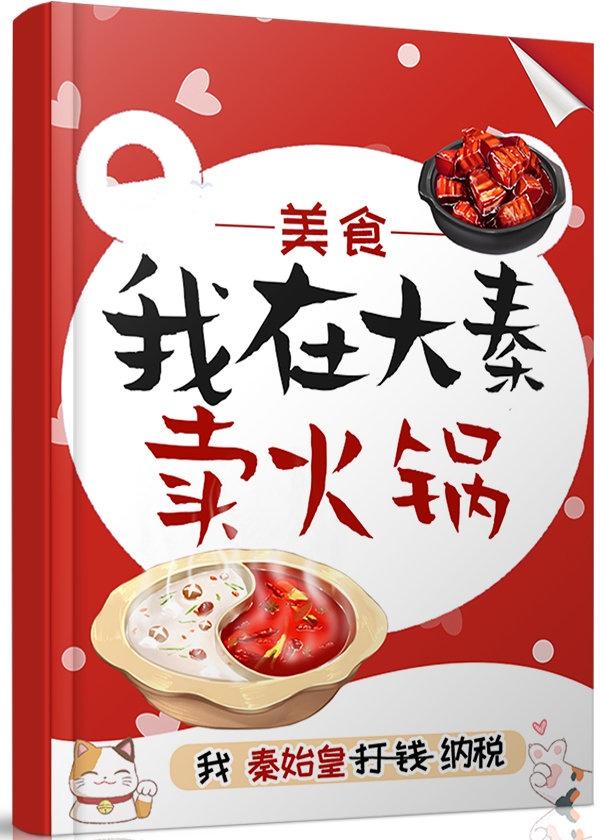极品中文>杀将令在线阅读 > 分卷阅读56(第2页)
分卷阅读56(第2页)
“该当何罪?”赫舍里隼突然仰天大笑,笑声豪迈又疯癫,道:“先帝在时,他只一句要统一天下,还天下人盛世太平,我就一心只随他东征西战,拓南北疆土,而今诚宜帝在位,我便一心为国不敢懈怠,皇上却为了讨好太后,听信奸人之言要至我于死地,我该当何罪?不如世子你来告诉我,该当何罪?”
曹错丝毫未乱,一一列举他的罪责,道:“临时叛变,投靠敌营,按律当斩,你认不认?”
赫舍里隼咬紧牙关,良久,他才脱口而出两字:“我认。”
见他没有抵赖,曹错继续列举:“举兵造反,欺君罔上,扰乱江山社稷,危害国家安危,其罪株连九族,你认不认?”
赫舍里隼并非汉人,而是游牧民族的子孙,生母是个低贱的歌女,他甚至都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又早丧,如今要株连九族,他赤条条一个人游走人世间,哪里有什么与他相干的九族?
他沉声道:“我认。”
曹错继续道:“勾结外族,包藏祸心,重伤我军将士,意图谋害皇上,你认是不认?”
“我不认,”赫舍里隼情绪起伏剧烈,据理力争道:“我投靠寒北,不是为了谋害皇上,而是想拖住他们,皇上要我班师回朝,各大世家能放过我吗?太后一党能放过我吗?还有以潘慧为的‘伶俐’书生的唾沫星子能放过我吗?我又有什么错?
“如今的朝廷,达官贵族个个儿把自己的钱库养得充盈丰满,真正在外卖命的将个开端,败的不是我。”
曹错只当他是为自己开罪才会说这些毫无意义的话,道:“我以为你是铁骨铮铮的汉子,没想到你也只是贪生怕死的鼠辈。”
赫舍里隼一生沙场征战,与无数刀剑博性命,不曾想老来却被一个毛头小子羞辱,他铿锵道:“我戎马一生,为大魏江山抛头颅,热血洒黄昏,想当年跟随先帝风里来雨里去,上刀山下火海我又何曾畏惧过分毫?我不怕打败仗,真丈夫从哪里跌倒便从哪里爬起,我兵败寒北,那我定要向寒北讨回来,可皇上居然听信宫中妇人妖言,让我前去竟京领罪。”
曹错:“你纵容营中骄横的风气,导致兵败寒北,难道不该向朝廷请罪?”
赫舍里隼练兵日长,怎么会不知骄兵必败之理,只是一场接着一场的胜仗让他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军中士气懈怠确实是兵败寒北的重要原因。
但是士兵之所以会懈怠,最根本的原因却不是什么骄兵必败的说辞,而是他们常年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就连拿在手里的长矛都生了锈,而朝廷拨下来的银子一拖再拖,拖到战事起了又息,拖到冬天去了又来。
现在到了这小子嘴里,兵败寒北的原因竟成了“骄兵必败”,赫舍里隼语气悲昂道:“我年过六旬,大不了就是一死,没什么可惜,可宁东之地一旦落入寒北之手,他们挥兵南下是迟早的事情,到那个时候,除了身经百战的秦王和涵南陆长宇能敌,朝中后起之秀还有谁能抵挡?如今陆长宇中风,他儿子只不过是个酒囊饭袋,你虽说勇气可嘉,却过于年轻经验不足,与明士羽对立简直天方夜谭。”
“你这么多说辞,无非是在为了你的叛变脱罪,”曹错冷漠地看着他,道:“你自己就是带兵的人,举兵造反,投靠敌营该当何罪你不会不清楚,我劝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这样做的后果只不过是徒增伤亡。”
“该当何罪?”赫舍里隼突然仰天大笑,笑声豪迈又疯癫,道:“先帝在时,他只一句要统一天下,还天下人盛世太平,我就一心只随他东征西战,拓南北疆土,而今诚宜帝在位,我便一心为国不敢懈怠,皇上却为了讨好太后,听信奸人之言要至我于死地,我该当何罪?不如世子你来告诉我,该当何罪?”
曹错丝毫未乱,一一列举他的罪责,道:“临时叛变,投靠敌营,按律当斩,你认不认?”
赫舍里隼咬紧牙关,良久,他才脱口而出两字:“我认。”
见他没有抵赖,曹错继续列举:“举兵造反,欺君罔上,扰乱江山社稷,危害国家安危,其罪株连九族,你认不认?”
赫舍里隼并非汉人,而是游牧民族的子孙,生母是个低贱的歌女,他甚至都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又早丧,如今要株连九族,他赤条条一个人游走人世间,哪里有什么与他相干的九族?
他沉声道:“我认。”
曹错继续道:“勾结外族,包藏祸心,重伤我军将士,意图谋害皇上,你认是不认?”
“我不认,”赫舍里隼情绪起伏剧烈,据理力争道:“我投靠寒北,不是为了谋害皇上,而是想拖住他们,皇上要我班师回朝,各大世家能放过我吗?太后一党能放过我吗?还有以潘慧为的‘伶俐’书生的唾沫星子能放过我吗?我又有什么错?
“如今的朝廷,达官贵族个个儿把自己的钱库养得充盈丰满,真正在外卖命的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