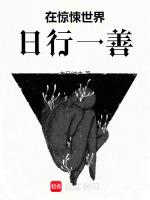极品中文>诱饵蛋白 > 第58章 缠(第3页)
第58章 缠(第3页)
早前,津德的二公子能力与陈渊齐名,号称权贵家族的“双骄”。
老爷子也稀罕他,分配家产时,长子50%,二公子40%,剩下的10%给外室,傍个身,养个老。
直逼长子的40%,让二公子离奇死于非命。
董事局上任的前夕,他在江滨国际会所应酬酒局时,无故猝死。
尸检的结果,排除非正常死因,说白了,命该绝。
业内传言,他是被下降头了。
津德的竞争对手,原配和三公子那房,说不准是哪个动得手。
高门大户的公子哥,尤其内定的继承人,对外公开的生辰八字全是假的。
甚至更谨慎的,几个儿子的生日,也互相不详。
生怕,被邪门歪道迫害。
防备一手,总没坏处。
陈政犹豫不决,何佩瑜在这时仰起头,憔悴得没一点血色,“我难受。。。”
他抚摸了她脸一下,问程世峦,“从什么渠道请?”
“我表侄女在泰国工作,有相关的门道。”
“不要大张旗鼓,悄悄请。”末了,陈政又补充,“钱不是问题,治好二太太,要多少数,给多少。”
何佩瑜整个人蜷在他怀里,眼珠动了动。
周末,陈渊和陈崇州同时接到陈政的电话,命令他们回老宅一趟。
陈渊那边,是安桥接的,他抽不开身,在会议上谈合作。
傍晚,陈崇州从医院下班,直奔老宅,门一开,皱了下眉。
碎瓷器,玻璃碴,从回廊迸溅到玄关,蜿蜒交错,空气中还蔓延着香灰、血腥的气味。
他望了一眼佣人,“怎么回事。”
佣人低着头,“大太太做法。。。害二太太,证据藏在阁楼。”
陈政那一辈,都信这茬,比如风水,运势,法事。再者,他年岁老了,耳根子也软。
可陈崇州只觉荒谬。
据说,程世峦请来的是泰国有名的小龙王,摆了蜡烛和法台,随即指出阁楼有脏东西。
阁楼是江蓉礼佛的地方,供奉了不少尊佛,定期打扫通风,平时,不许保姆进出。
如此避讳的习惯,导致翻出“血盅”后,陈政深信不疑她是幕后黑手。
陈崇州绕过屏风,走进客厅,陈政在沙发上,身边是何佩瑜,江蓉站着,神情决绝凛然,“我如果害她,天打雷劈!”
“你没害她?佛堂的钥匙,只你有。”
方姐在一旁说,“佣人也有钥匙,先生,您别冤枉了太太。”
负责阁楼的佣人面孔吓得一阵青一阵白,“先生,太太,我不敢!”
江蓉看着何佩瑜,“我再恨透她,出手也该隐蔽些,在老宅的佛堂里,我愚蠢到这地步吗?究竟是谁陷害谁。”
何佩瑜痛哭流涕,“江蓉姐,陈渊是长子,崇州没他尊贵,陈家的一切都是陈渊的。我只求老二无病无灾,不要像我第一个儿子的下场。我不争不抢,甘心屈居你之下,你也容不了我们母子吗?”
做个法,没抓现行,倒有转圜。
提起儿子,果然激起陈政的怒火,他绕过茶桌,逼近江蓉,“佩瑜怀陈腾6个月,你知晓是男孩,为取代她,对陈腾下毒手,事后你不承认,直到司机指证你,你辩无可辩,才认。这些年,你认为我忘了?那是我的亲骨肉!念及陈渊,我忍了而已。江蓉,你当了三十五年的陈夫人,也风光够了。”
陈政背过身,“以后,大大小小的场合,佩瑜出席就好。你在佛堂,拜你的佛吧。”
“你什么意思?”江蓉瞪大眼,“陈政,你一把年纪,要再娶吗?万宥良将女儿嫁给陈渊,是看重他原配长子的身份,你离了,还打算联姻吗。”
“我不会离婚。”他注视墙壁上的画,“因为你,影响我声誉,不值。”
其实,何佩瑜知道,她至死也上不了位。
陈渊这场联姻,捍卫住了长房的尊贵。
她只图,攥住女主人的实权,架空江蓉,无所谓虚名。
为此,她才演这出戏。
她掐准了,上流圈最忌讳什么,陈政又一向多疑,这招,江蓉难以翻身。
何佩瑜脸上浮起一丝得意,朝江蓉眨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