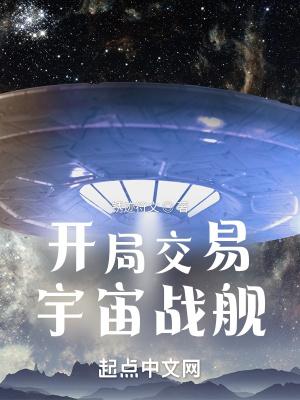极品中文>背叛的图片 > 第90頁(第1页)
第90頁(第1页)
「早上好。你在算錢麼?」
我走到甚爾跟前,用手指撫摸他緊鎖的眉毛。
到處都很亂,沒有立足之地,甚爾便伸手將我抱上大腿,主動當起椅子。
「是啊,要去學習的話,鋼琴是必不可少的吧?」
「不是說早上腦子比較清楚麼?煮粥沒有事情干,就順便清點下生活費。」
年輕的男人將臉埋進我的頭髮,深深嘆息:
「……但不行啊,我果然不擅長算數。」
跟沒有個人儲蓄、錢有多少花多少的過去相比,他願意拿筆算算財產,就意識而言已稱得上進步顯著。
「真體貼,這樣分別放好已經很清楚了。接下來讓我幫幫你吧。」
對他的理財能力沒抱任何指望,我理所當然拿出了誇讚孩子的態度,撫摸他頸側細小的絨毛,抬頭親吻他抿住的嘴唇。
不願意被當孩子看待,他從喉嚨里擠出一聲抱怨的咕噥,但手指倒是相當親昵地爬上後背。
後面甚爾撥開雜物,盤腿靠在一邊,看我跪坐在地毯上工作。
對於擅長精密咒力操作的我來說,這種基礎的加減計算並不需要藉助紙張。
漆黑的影子是精準的「點鈔機」,一條緊壓鈔票末端,另一條做出翻書的動作,「沙沙」幾秒我就能算出總額。
由於在商場的隨意揮霍,就算有紘子的報酬作為補充,厚度也減了大半,再扣除鋼琴的價格,基本已經所剩無幾,再保持現有的生活水準,不到一周就會見底。
好在從禪院家還帶出了不少珠寶。
原來我只要看圖冊選擇喜歡的款式,並不了解印在珠寶盒上的商標含義,現在去了商場才知道那是奢侈品牌的私人定製款式。
比如這條作為流光溢彩的鑽石項鍊,就算拆成碎鑽,刨除設計費用,價值劇減,流通到黑市上也有一台鋼琴的價值。
作為我們第一次一同參加宴會的禮物,直毘人曾笑著將它系在我的頸子上:「現在國外年輕女孩子會帶的東西,我倒不太欣賞這種耀眼的美。但……是不是比較活潑呢?」
為了好好欣賞「禮物」,我還專門換上了與之相稱的抹胸洋裝。
可鑽石沉重又冰冷,它們貼緊蒼白的皮膚與嶙峋的鎖骨,比起鮮紅一點的「未盡之言」,更叫人毛骨悚然。
對送出的禮物從不過問,直毘人大方到不拘小節,同時吝嗇得讓我憎恨。
被他堆砌出的價值哄騙,想想就讓人生氣,報出價格之後,我冷冷地將它們推到了一邊。
「全賣掉?不留幾件喜歡的。」
「不需要、我討厭這些東西……」
唯一沒那麼排斥,還有那條「小鳥」手鍊,我將它從影子裡掏出,用來轉移甚爾的注意力:
「我已經有最喜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