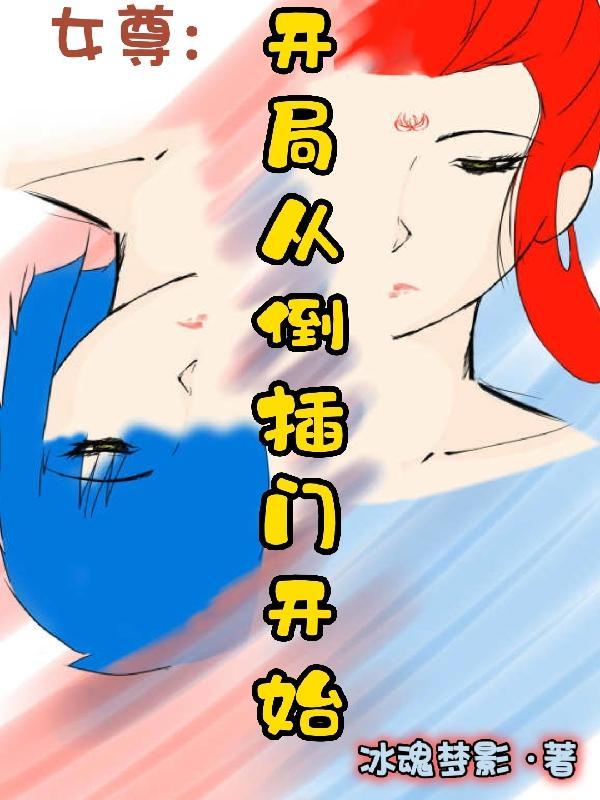极品中文>后宫诱逃花腔 > 第9页(第2页)
第9页(第2页)
“什么手?”宁若言一脸茫然地看着方湄。
方湄冲着他系扣子的手努了努嘴:“你的左手,拇指。还在流血。”方湄放下削好的苹果,走向卧室。
“哦。”宁若言把拇指放进嘴里吮着,含糊地说:“没事儿。”
方湄在卧室里扬声问:“会熬通宵吗?”
“可能吧。你别等我,自己先睡。”宁若言走向大门,没有回头。
听到门响,方湄手里的创可贴从指间飘落,打着旋,颤抖着,落在地上。
宁若言狠狠拍了两下电梯的按钮,看着那不变的楼层数,转身进了楼梯间。
从17层飞奔而下,既使是在10月末微寒的夜晚,宁若言的额上还是沁出了汗珠。
停车场管理员拦住气喘吁吁的宁若言说:“宁律师,有个人一直靠在你的车上,他说是等你,你快去看看认不认识他,没准儿是个偷车贼呢。”
“我知道。”宁若言如一阵风般掠过管理员,飞向自己的车位。
站在离自己的车还有两米远的距离,看着黯淡光影下那个熟悉的身影,宁若言喘着气,竟迈不动脚步了。
依靠车门而立的温冬听到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抬起头,倏地站直身体,大步走向站在高楼阴影下的宁若言,一把把他抱在怀里,几乎要把他按碎、压进自己胸膛的搂着他。
宁若言不知道是怎么把车开到凯莱的,也不记得是怎么进的房间。只记得温冬一进房就衔住了他的脖子,唇在他的颈项间如火般碾转着,手不停地撕扯他的衣服,在他冰凉的肌肤上挑拔着。
感受着胸膛上麻痒的刺痛,宁若言闭着眼轻轻地呻吟着,扭动着腰。抚在腰上的手缓缓移到身后,冰凉滑腻的膏体随着手指的转动一点点的进入体内。宁若言抬起双腿攀附在温冬的身上,扭动的腰肢一点点提起,迎合着手指的深入。
温冬抽出手指,翻转宁若言的身体,吻着他的肩和后颈,又轻轻吻着他略凸出的脊椎骨,下体轻轻用力,一点点地顶入。宁若言大声地呻吟起来,随着温冬在身后一下下的撞击,叫出了声……
温冬伏在宁若言的身上,吻着他的唇和下巴,宁若言抬起手撩拨着温冬额前被汗水濡湿的头发,温冬拉过他的手吻着。
发现宁若言拇指上仍在流血的伤口,温冬抬起头问他:“怎么弄的?”
“是你弄的。”宁若言有些不好意思,要抽回手,却被温冬含在嘴里,轻吮着。
感到宁若言身体的变化,温冬放开他的手指,吻着他微闭的眼睛说:“你真敏感。等一会儿再给你。”
宁若言闭着眼,感到温冬离开他的身体,爬下床,过了一会儿,又爬回床上,拿起他的左手,受伤的拇指被包裹住……
宁若言睁开了双眼,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因染上了欲望的色彩而浮起一层氤氲。他欠起身,将唇凑近温冬,主动吻着他的唇。温冬回吻着他,顺势又把宁若言扑倒在床上。
两具身体再次缠绕在一起……
温冬几乎每个周末都从宁波飞回北京,和宁若言像要融化彼此般的需索着,周日再飞回宁波。
一周一次的相逢却使宁若言对温冬的思念愈加强烈。他开始每天数次登陆事务所内部的tra,一上去就直接进律师介绍,然后在搜索里机械地敲下“wendong”几个字母。
他常常开着介绍温冬的页面,对着温冬那张严肃的证件照长长久久的凝视着。照片里,温冬垂落的额发覆盖额头的面积,英挺浓密的双眉飞扬的角度,翦翦双目注视的方向,领带的图案等等细节,都印在宁若言的脑子里。照片下的文字介绍,宁若言已能背诵,连哪个单词换行都记得清清楚楚。
宁若言不清楚自己对温冬的渴望和感情算什么。他虽然没有单蠢到不知道同性恋是怎么回事,但了解程度仅限于大学期间,和同学以局外人的身份进行的闲聊。现在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当事人”,却对自己的心情完全不了解。但他清楚地知道,过去那个重心灵、轻肉欲的宁若言只是个假相,真实的宁若言,是个十足的、被欲望所操纵的野兽!
对于方湄的感情呢?他不知道那算不算日久生情,毕竟和方湄在一起已经六年多了,一切都习惯成自然。但宁若言可以肯定一点,从认识方湄那天起到现在,他对方湄从没有过激情和渴望。正视到这一点,让他痛恨自己,对方湄充满歉意。如果没有遇到温冬,也许他会和方湄结婚、生子,平淡的过一辈子。但是,现在,他不敢让方湄知道真相,他小心翼翼地掩藏着,努力让他和方湄的生活一如从前,没有任何起伏变化,包括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