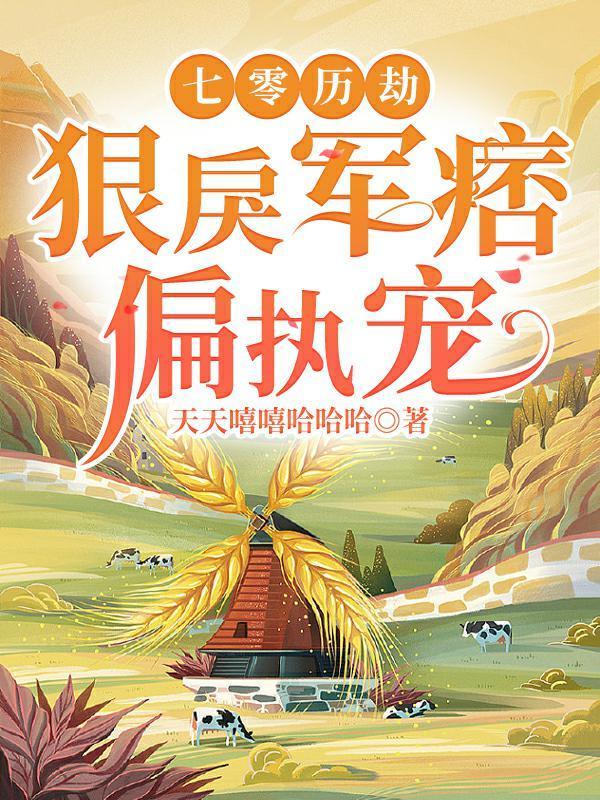极品中文>蒙尘珠演员表 > 第26頁(第1页)
第26頁(第1页)
在風塵中討生活的人,心眼最是多。凡是一切可能被當做把柄的事物都被他處理得乾乾淨淨。
此時這琴匣中的只是一張普通的琴,而真正的靈犀琴早被雲舟藏在了更深的地方。
珠碧想借王爺之手毀掉他珍愛的東西,只可惜,道行太淺。
只是如今真正的靈犀琴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出現了,否則到時就不是一百戒尺可以解決得了了。
溫存了半天之後,蕭啟將琴匣放到珠碧手中:「答應你的事本王兌現了,這把琴送給你,這回滿意了罷?」
珠碧打開琴匣,烏黑的琴身靜靜躺在其中,他原先並不曾仔細見過真正的靈犀琴是何模樣,因此也不懷疑此琴真假,良久後酸溜溜地答了一句:「珠碧以為是多好的一把琴呢,原也不過爾爾。」
末了,還看他一眼,將挑釁二字盡數刻在了那黑白分明的眼底。
這種蹬鼻子上臉的行徑著實可恨,可惡。
更可恨是蕭啟,對這賤貨尚鮮著,是以無條件縱容。
雲舟暗自咬碎一口銀牙,細長瑩潤的手指幾要生生揉碎身上衣料。
這番話聽在耳朵里也不惱,只是拍了拍他的腦袋,笑:「蹬鼻子上臉了?」
話音一落,他將雲舟打橫抱起,雲舟嬌喘一聲,旋即摟緊了蕭啟的腰,轉過頭來,留給珠碧一個嘲諷的眼神。
珠碧原本就不是真想要這把琴,只是想看雲舟的好戲罷了,誰知他倆又當著自己的面摟摟抱抱,心中實在是憤懣不平。
蕭啟抱了雲舟往塌上去,只淡淡地留下一句:「珠碧,時辰不早了,乖乖回去歇息罷。」
珠碧哪還敢再留,咬唇道了句是便灰溜溜地出去了。
雲舟今夜並不好過,翌日一早,他傷痕累累地躺在鎖雲台的塌上,睜眼是滿目仇恨。
珠碧,來日方長,我與你不死不休。
此事過後,這兩位的梁子便算徹底結下了,從此後一見面便是你來我往的明槍暗箭,心裡盤算的歹毒算計層出不窮。
雲舟的手段之陰險比起珠碧不遑多讓,只是,他到底良心未泯,陰險歸陰險,卻從未真正想要珠碧的命。其實也不單是為那可憐的一點點良心,最重要的,還是要留著珠碧與他共同分擔來自蕭啟的雷霆雨露。
善惡是非僅一念之差,雲舟不曾想到,自己的寬容,反將自己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從雲舟瞞著蕭啟藏起真正的靈犀琴之後就已騎虎難下,註定了真琴泄露之時,就是他大禍臨頭之日。
不論南館還是朝堂,人一旦被誰捏住了把柄,便等於將性命全數交到了那人手裡,結局往往悽慘,不得善終。
假的靈犀琴被蕭啟奪來賜予珠碧,珠碧就將之坦蕩蕩放在萃月軒中,閒來無事便信手撥弄,直到某一日來了個愛琴成痴的恩客,此人是楊清逸的狂熱仰慕者,自然識得楊清逸的佩琴。
他起初看著這把琴便隱隱覺得不對勁,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但珠碧一口咬定這就是靈犀琴,面上還隱隱顯出不悅之色。但恩客不肯就此罷休,按理說樂者對自己的樂器最是愛惜,怎會將之隨意贈給別人呢?此番被他撞見了,他定要知道其中原委。
「我可以彈彈麼?」
「爺好生無!奴都光著身子站在爺的面前了,爺連看我一眼都吝嗇,眼裡只有這把琴!爺若真愛琴如命,來甚麼南館狎甚麼妓?出門右拐過三條街,那裡一整條樂館,不比這裡有意思!」
恩客一時無言,還是看著桌上的琴,像流連糖果攤的小童,不肯挪開。
……
珠碧無語,他倒也不敢真的惹怒恩客,取來紗衣披身,慵懶地撥了撥散發:「罷了罷了,爺想彈便彈,奴家在塌上等您。」
於是琴音在指尖流瀉,不過片刻,恩客便按弦止音,隨後擲地有聲鄭重開口:「此琴,並非靈犀。」
作者有話說:
領便當倒計時,唉
第14章東窗事發
——此琴,並非靈犀。
珠碧心中如遭一記重錘,將眉一皺,檀口微張,臉上浮現出一絲薄怒:「這等事情,爺可別胡謅!」
那人十分肯定:「楊清逸前輩還未入仕時,曾與另一樂壇名家於西陵山枕風台上鬥了一天的琴,在下有幸,曾親耳聽到楊前輩以靈犀琴彈奏《胡笳十八拍》,其聲如金玉,氣貫長虹,將山中百鳥都引來了。」
恩客提及此事便不由得面露崇敬之色,抱起面前琴摸上琴身細細摩挲:「此琴顯然是有意模仿靈犀琴的外形,但外形易仿,琴聲難仿。我方才撥動此琴,其聲既濁且澀,與真正的靈犀琴相去甚遠。」
知道了真相的珠碧駭然當場,卻留了三分竊喜,此琴若真是假的,便說明雲舟給他的就不是真的,真琴必定還被他藏在鎖雲台里,難怪當時王爺要他交出琴來他反應那么小,原來他早就留了這一手。
此番捏住了雲舟的大把柄,有這人在,扳倒雲舟已不是難事。
雖知如此,珠碧依舊不敢輕舉妄動,唯恐事有變數。後來幾經謀劃,終於當著蕭啟的面拆穿了一切。
起初雲舟面如止水波瀾不驚地否認,直到蕭啟的近衛抱著真琴出現在眾人面前,與假琴放在一塊時,雲舟才徹底慌了神。
肝膽俱裂地望向蕭啟,幽深的眼眸里竟含了幾分令人膽寒的笑意,他轉動手中茶杯,不言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