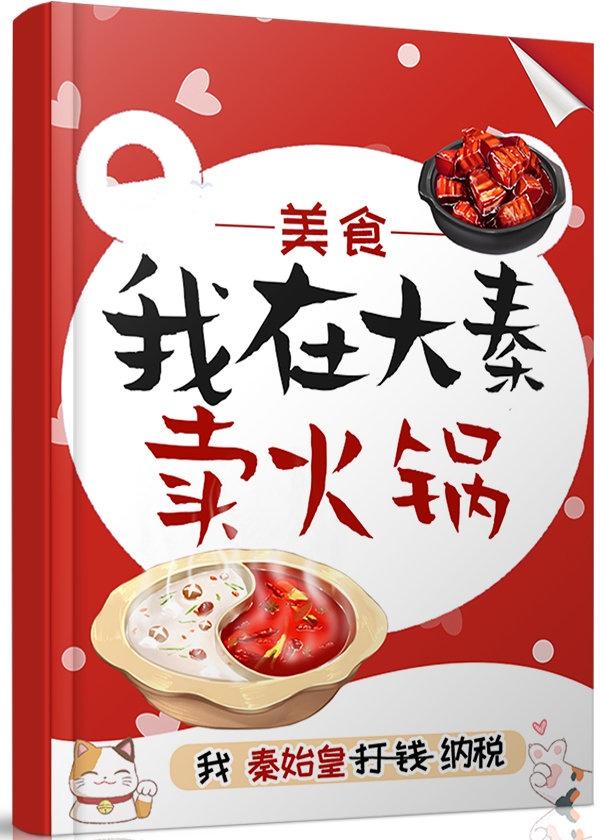极品中文>溪春鱼竿 > 朦朦(第1页)
朦朦(第1页)
仔细地将江闲身上的伤处理好后,陈檀溪便强行把他赶去休息,自己一个人来到小厨房。
心不在焉地忙活了半天,待糕点上了蒸锅,陈檀溪终于忍不住在心中唤道:“破王八,你在吗?”
机械的声音缓缓道:“宿主,请你下次叫我的本名,零。”
“好,小零,”陈檀溪默默加了个字,“我要问你一件事。”
“请说。”
陈檀溪的表情难得严肃起来,迟疑道:“虽然我继承了原身的记忆,会受到一定的情绪影响也正常,可是刚才对着江闲,我不应该那么失控才对。”
江闲是陈檀溪七岁那年在应州寒江边捡到的。
当时正值隆冬,跟着父母去探望祖母的陈檀溪缩在暖融融的马车里,长途跋涉使得她有些无聊,便随手掀了车窗帘子,隔着风雪与那匍匐在地狼狈不堪的男孩子对上了目光。
出于恻隐之心,陈檀溪开口央求父母将他带上了马车。
无父无母的小乞儿,被陈檀溪取了江闲的名字,派人精心照料了起来。待到陈檀溪一家要返程之时,养好了病的江闲跪在陈父面前,发誓自己一辈子都会效忠陈家,请求跟在小姐身旁做一名侍卫。
一个六岁的小娃娃,路走稳还没几年,能当什么侍卫?陈父虽是如此想,但架不住陈檀溪也苦苦哀求,便大手一挥同意了,权当是给女儿寻了个玩伴。
不料江闲竟是说到做到,自进了陈府门便日日早起,一个人在后院里练拳舞棍,每次都要练到大汗淋漓。
陈父被他这般的认真坚持触动,自己只要在府里便会指导一二,又送了几本书给他自学,后来更是给了他一块腰牌,叫他去盛都兵营里历练历练。
江闲本就颇有天赋,加上日复一日的刻苦,身手早已是出类拔萃,又兼头脑冷静机敏,若是参军,领兵封将亦不是问题。
然而十年过去,江闲仍如最初般守着陈檀溪。
原主自然与这忠心耿耿的小侍卫很有情谊,但也只限于主仆之情。可是方才自己看着江闲身上的伤,只觉心口揪成一团疼得要碎了般,眼眶酸涩难忍,难过的情绪扑天盖地而来,脑海中更是闪过一些快到捉不住的记忆片段,直让人心神恍惚。
“还有上次在酒楼和景乐衍,”陈檀溪顿了顿,接着道,“那时我回想起来的记忆,并没有在原主的记忆里找到——换而言之,那是我自己的记忆,对吗?”
零沉默着,并没有应答。
陈檀溪权当它默认了,皱眉思索着:“这么说来,我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这个世界?可我明明才来不到两月,究竟是怎么回事?”
零终于开了口:“宿主,不要再问了。到时您自然会知道的。”
陈檀溪便听话地闭上嘴,脑中却仍是乱糟糟的,隐隐透着疼。
这样懵懵懂懂的感觉实在不好受,心里空落落的,一时间仿佛坠入迷雾失去所有方向,什么也抓不住看不清般。
陈檀溪竭力不再去想,仔细将食盒清洗备好,正巧糕点也到了时辰,便装进食盒里准备去陈渊的院子。
谁知脚还没迈出厨房门,到是陈渊身边的小厮青果先满头汗地找了过来。
陈檀溪见他这样心里就打突,忙问:“兄长找我?你可知是何事?”
青果抹了把脸上的汗,急得直结巴:“不是大公子找,找您,是是是,大公子他,他他——”
“你别急,慢慢说。”
青果长长呼出一口气,哭道:“宫里传来消息,大公子不知因何事触怒了龙颜,今日早朝被罚跪两个时辰,现在人已经晕过去了!”
陈檀溪有些茫然:“你说,兄长被罚了?”
“是……”
恍然回神,陈檀溪掩下心中惴惴,快速地做了决定:“人可是还在宫中?去备马车来,我去接兄长回家。”
青果惊得连连摆手:“小姐不可啊!”
“你慌什么?又不是去劫狱,”陈檀溪将食盒放回灶台上,“兄长一向为国尽心尽力,想来所犯也不是什么大事,圣上必有英明决断。若圣上不同意我进宫接兄长,我便在外等着便是,哪里还能出了错不成?”
青果无法反驳,只能应了是,匆匆地下去安排了。
陈檀溪回头望了眼精心准备的食盒,叹了口气。
但愿不是什么大事吧。
宫门巍巍,红墙高耸,天色透着阴,似是要下雨了。
陈檀溪下了马车,叫车夫去旁候着,自己便朝宫门处去了。
门前立着两名银甲守卫,陈檀溪深吸一口气,试探着问道:“两位守卫大哥,能否请问陈渊陈相是否在宫中?”
两名守卫对视一眼,其中一个答:“陈右相还未曾出宫。”
陈檀溪便解下腰牌,恳求道:“那不知可否劳烦为我通报一声,我想进宫见陈相。”
闻言,先前答话的守卫上下打量她一番:“你……你是陈小姐?”
“正是。”
守卫摇摇头:“陈小姐,您身上一无官职二无诰命,属下不能随意做主为您递牌子进宫。”
“再说,”那守卫压低声音,“现在宫中谁人不知道陈右相被罚?陈小姐,听我一句劝,莫要在这当口触霉头了,快些回府罢!”
陈檀溪心知进宫是不可能了,便轻声道:“多谢守卫大哥提醒,只是我到底放心不下家兄,便在外等着吧。”
守卫不再多说,由着陈檀溪到一旁等候了。
风云翻涌,天不知何时暗了下来,自乌云中淅淅沥沥滴下些雨来。
陈檀溪被这凉雨挨着身,不由瑟缩了下。
车夫气喘吁吁地跑来,懊恼道:“小姐,老奴大意,走得匆忙未曾带伞,车上唯一一把竟然坏了架子破了洞!小姐,先跟老奴乘车回府去,拿了伞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