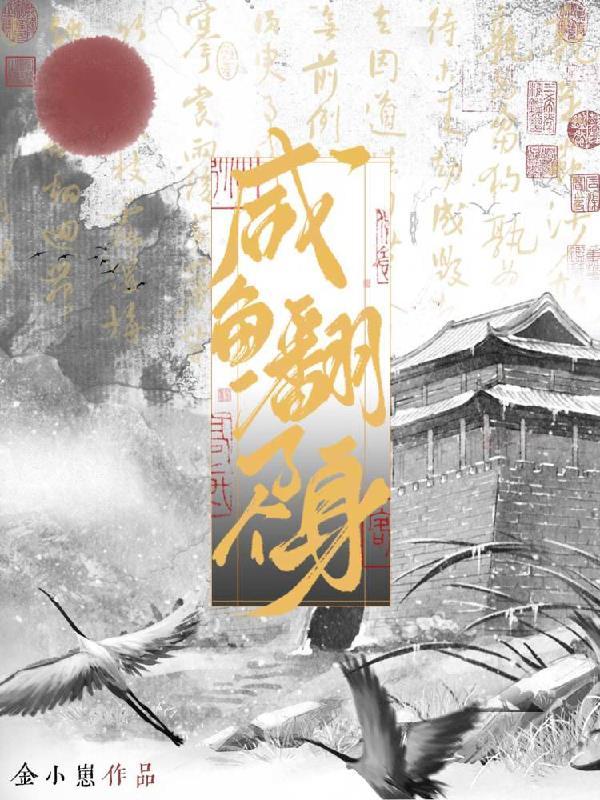极品中文>我们已经和离了姜玥番外 > 第19頁(第1页)
第19頁(第1页)
禮部侍郎看過他的文試答卷,一邊讚賞「文采拔俊,越流輩」,一邊把春祭大典祭文的草擬託付給他。
寫一篇這樣的祭文,不難,只耗費些心力。
類似的事情有了開端便接二連三,短短几日,沈徵案頭擺滿有待落墨的各類祭文、碑文、提序。
沈徵一概應下。
有些東西他可以推脫,比如散值後的應酬交際;有些東西他不能,比如本在職責內的論撰文史,恰好以此拒謝琿。
沈徵圈出有待修改的地方,做個記號,把數疊折本推到謝琿面前,「我若去了,這疊,還有摺疊,你代筆?」
謝琿隨手一翻,「花里胡哨的,你閉眼也能寫十篇。」
「難道……」謝琿想起一事,「上次姜府宴會,我看鄭小娘子好像對你有點意思,就問你問題的那小娘子,我記得她的聲音,特別脆亮,道麟你是不是想避嫌?」
是避嫌,卻不知是避誰的嫌。
沈徵一頓,狼毫在紙面落下過分墨色濃稠的一撇。
謝琿點著那團墨瞭然:「我說中了。」
「如何說中?」
「你一心二用,一邊應付我聒噪不休,一邊落筆,整篇都沒寫錯一個字,我一提到鄭小娘子就寫岔了。」
「事關女子聲譽,莫要胡言亂語。」
「這裡又沒有別人。」
謝琿掃視,值房只設二員當值,沈徵的輪值同僚有事去隔壁衙司,他才敢這麼明目張胆地說私事。
沈徵不再接話。
謝琿湊近觀察,看他表情毫無破綻,沒有被說中心事的心虛,不由得嘆了口氣:「真對流月峰沒興,那罷了,我不愛強人所難。那我走了,道麟,我真的走了?」
沈徵抽出一張嶄羅紋紙,重謄寫方才擬定的祭文。
謝琿一拖三頓的腳步聲,終於慢騰騰地遠去。
狼毫筆撂下,他揉了揉從今晨起隱隱作痛的太陽穴。
昨夜只睡兩個時辰,去關心一匹馬有沒有被栓在石獅子上這種蠢事,做一次就夠了。
整整一晚,一閉上眼。
沒有繁複金鈴,也沒有丹紅水袖與鵝黃襦裙,只有粗布縫製的布裙,美人腰如束素,垂墜烏髮如綢。
她赤著雙足,踏在河邊細軟的茵草上曼舞。
只給他一人跳。
-
流月峰是京郊名山,山體寬闊綿延,由數十座起伏錯落的山峰組成,山內環繞一方風景明秀的玉衡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