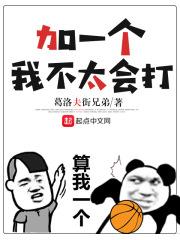极品中文>通灵少女台剧 > 第四十八章 汇集万千思绪(第1页)
第四十八章 汇集万千思绪(第1页)
回到家后,父亲看着叶隐给云西写的那封信,神思道:“你们不觉得叶隐像是故意把这封信留在现场,让我们现的吗?如果叶隐有一个心上人,他怎么会把她的名字暴露出来,让我们知道,然后通辑她呢?
我仔细想了一下,然后说:“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故意引诱我们,拖延时间。”清明点了点头,然后说:“还有很奇怪的一点,叶云为什么不把封印石埋起来呢?他那么狡猾,最起码得把它埋起来吧?”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后来得知,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清心小区是叶云最后封印的小区。他在进行封印时,刚好被附近的抓捕团看到了动静,慌乱下把封印石投到了井中,决定事后再来掩埋。
未成想,他第二次带着手下来清心小区,走的是一条秘密通道,抓捕团正好派人埋伏在秘密通道旁,叶云寡不敌众,被抓捕起来,先关到狱中一段时间,然后执行死刑。狱中的这段时间内,叶云的心脏病日益严重,没来得及写遗书就猝死了。
他死后,托梦给了他的儿子,让他到清心小区内把封印石埋好。谁知他的儿子才二十岁,不像他父亲那般心思缜密,是个粗心的人。他接到父亲的指示后来到清心小区门外,从笼罩在小区上方的阴霾判断,小区已经被封好,无需他再操心了。他就这样报告给了叶云,叶云也放心了。
事情就是这样。让我回到现实。突然,楼下一阵骚动,我从窗户往楼下看,看到几个抓捕团的警察正押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眼里都是泪,看上去像被冤枉了。“那是云西吗?走,拿上那封信,跟上去看看。”清明说。父亲说:“叶隐很像是嫁祸给她的。不过他能从城中顺利逃走,大概率是因为有一个人在一直暗中帮助他,和信上写得差不多。”
我们拿着那封信冲下楼,跟上抓捕团。警长一见着我们,就热情地说:“你们可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谢谢你们。作为回报,我们不愿像普通警局那样给你们钱财,我们决定邀请你们,参加对云西的审讯,我们原本以为物证已经够多了,谢谢你们又送来一封信。”
父亲只是默默地跟着,没有回答。云西一路上一直在啜泣,小声地说着:“我不知道什么通灵……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们毕业后就再也没联络……”父亲也以极小的声音念叨着几个词:“故意……栽脏陷害……”过了一会儿,到了抓捕团门口,在警长开门时,我偷偷地观察着云西的神情:她看上去非常震惊,好像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开门方式。还没开始审讯,我对她的疑虑就打消了一半,她可能真的是一个被人利用的普通人而已。
审讯开始了。警长给他戴上了检测记忆的仪器。面对警长的审讯,她显得毫不知情,甚至是不知所措。她的样子很可怜:长长的头披散着,显然是在睡觉时被拖了出来,她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一片惨白,手握成一个拳头,正在瑟瑟抖。,
回到家后,父亲看着叶隐给云西写的那封信,神思道:“你们不觉得叶隐像是故意把这封信留在现场,让我们现的吗?如果叶隐有一个心上人,他怎么会把她的名字暴露出来,让我们知道,然后通辑她呢?
我仔细想了一下,然后说:“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故意引诱我们,拖延时间。”清明点了点头,然后说:“还有很奇怪的一点,叶云为什么不把封印石埋起来呢?他那么狡猾,最起码得把它埋起来吧?”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后来得知,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清心小区是叶云最后封印的小区。他在进行封印时,刚好被附近的抓捕团看到了动静,慌乱下把封印石投到了井中,决定事后再来掩埋。
未成想,他第二次带着手下来清心小区,走的是一条秘密通道,抓捕团正好派人埋伏在秘密通道旁,叶云寡不敌众,被抓捕起来,先关到狱中一段时间,然后执行死刑。狱中的这段时间内,叶云的心脏病日益严重,没来得及写遗书就猝死了。
他死后,托梦给了他的儿子,让他到清心小区内把封印石埋好。谁知他的儿子才二十岁,不像他父亲那般心思缜密,是个粗心的人。他接到父亲的指示后来到清心小区门外,从笼罩在小区上方的阴霾判断,小区已经被封好,无需他再操心了。他就这样报告给了叶云,叶云也放心了。
事情就是这样。让我回到现实。突然,楼下一阵骚动,我从窗户往楼下看,看到几个抓捕团的警察正押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眼里都是泪,看上去像被冤枉了。“那是云西吗?走,拿上那封信,跟上去看看。”清明说。父亲说:“叶隐很像是嫁祸给她的。不过他能从城中顺利逃走,大概率是因为有一个人在一直暗中帮助他,和信上写得差不多。”
我们拿着那封信冲下楼,跟上抓捕团。警长一见着我们,就热情地说:“你们可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谢谢你们。作为回报,我们不愿像普通警局那样给你们钱财,我们决定邀请你们,参加对云西的审讯,我们原本以为物证已经够多了,谢谢你们又送来一封信。”
父亲只是默默地跟着,没有回答。云西一路上一直在啜泣,小声地说着:“我不知道什么通灵……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们毕业后就再也没联络……”父亲也以极小的声音念叨着几个词:“故意……栽脏陷害……”过了一会儿,到了抓捕团门口,在警长开门时,我偷偷地观察着云西的神情:她看上去非常震惊,好像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开门方式。还没开始审讯,我对她的疑虑就打消了一半,她可能真的是一个被人利用的普通人而已。
审讯开始了。警长给他戴上了检测记忆的仪器。面对警长的审讯,她显得毫不知情,甚至是不知所措。她的样子很可怜:长长的头披散着,显然是在睡觉时被拖了出来,她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一片惨白,手握成一个拳头,正在瑟瑟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