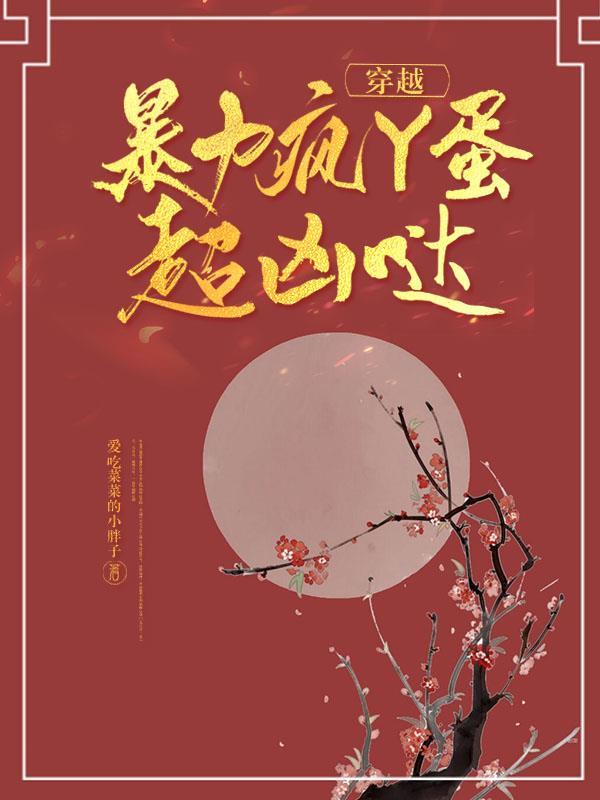极品中文>追风赶月莫停留 平芜尽处是春山 出自华夏说 > 第29节(第2页)
第29节(第2页)
她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挑破了两人之间模糊的关系。
他在逃避问题,也在逃避她。
她对一切都有着耐心,无论是对于马儿,还是男人。她的第一选择从来都不会是逃避,遇到问题,那就解决问题。在困难的麻烦,也总有解决的措施。
这件事不着急,走出了一步,下一步还要等一个时机。
日子一天天过着,她没有告诉孙建发自己坠马的事,每天还是照样地练马。直到这天她下了马,发现花生的背上鼓了个包。
包在脊梁上,就是铺马鞍子的地方。
她站在马边,轻轻戳了戳鼓包,里头的脓水软软的,看着她心里都疼起来。
她知道,这是她骑马的姿势不对。她因为做不好压浪的动作,每每被马弹起来,都会重重地在马背上砸下去。
这几天客人越来越多,孙建发几乎没有时间来教她。她看着网上的教学改良自己的动作,虽然比刚开始练的时候已经好了不少了,却也还是伤了马背。
她等到孙建发带着客人回来,把脓包指着给他看。
“师傅,这要请兽医过来看看吗?”
孙建发没说什么,就从鞍房里拿了根针来。针在打火机上一烧,扎进了脓包里。
又黄又稠的脓水从脓包里流出来,他又上手去挤,挤出了一点血水才了结。
安荞摸了摸花生的脖子,轻轻安抚它:“乖乖,对不起。”
“没事,马打背了很正常。”
她安慰马,师傅安慰她。
脓包破了,皮也挑开了,背上便是一大块破损。师傅在鞍房找出来的药膏只剩下了一点点,他打了个电话问孙成借,孙成让他去马队找苏德拿。
孙建发正要上摩托过草滩,安荞主动提起:“我去吧。”
“也行。”
师傅把钥匙给了她,她跃上摩托,车把手一转,越野摩托轰轰地飞了过去。
正值周日的午后,京津冀过来的客人们基本都踏上了归程,草滩上的马和人都不多,安荞的摩托骑得很快,又稳健地停在了马队门口。
苏德恰好要出门接个水,一抬头看见她。
“师傅让我来拿一下药。”
苏德:“什么药?”
“花生打梁了,破了块皮。”
苏德点点头,又转身进了合作社的铁棚子。
对于养马的人来说,马打梁是件常有的事。不注重的马主,便让马自己养着伤。稍稍心疼马匹的,就用点药。
他拿出来两支药膏交给她。
安荞接过药,抬眼看着他,忽然笑了笑:“没有想跟我说的话?”
苏德不语,她当然也不给他施压,跨上摩托就要走了。
钥匙转动,离合轻放,她却听到身后男人开了口:“腰还疼吗?”
她回眸一笑,眼睛闪亮亮的:“疼的。我自己买的膏药又快用完了,你还打算送我吗?”
“傍晚给你拿过去。”
“好。”
起风了,安荞别在耳后的头发被吹散。
她的头发虽然不长,却乌黑柔顺。被风吹皱了,反而有一股野性的美感。
摩托一响,她在风里远走。
回到自家的马场,安荞学着师傅给马涂药的手法,在花生破损的脊背上抹上了药膏,又把它带回了马圈里,让它能够安心休息。
眼看着风越刮越大,师徒俩都坐在鞍房后面躲着风。
孙建发忽然提起:“后天有一个长线的野骑,往上穿到内蒙交界。一共四天,要带十个客人。”
安荞前几天听他和孙力交流,已经得知过长线野骑的消息。
近些年马背旅行逐渐成为潮流,由马倌们带领客人一路骑着马,在草原或湖畔进行一定长度的漫游。这对于客人本身的马术基础有一定的要求。
当然,也很考验组织者的规划能力。
毕竟骑马还是相对来说较为危险的项目,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岔子。
安荞仔细听着师傅讲他的安排。
“从咱们这里出发,往山后的马道一路向北走,但不走那条绕回来的常规路线,从北面的村子里穿过去,就到了牧区的草场和公路。到时候,保障车就在公路上走,领队和客人就从草地上骑马……”
四天的路线规划、住宿饮食,孙建发讲得事无巨细。
安荞本以为他是想讲一遍给她听,顺便也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可他的话越说越细,她也觉察出不对劲的地方。
等孙建发讲完了,她才问一句:“师傅,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做导游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