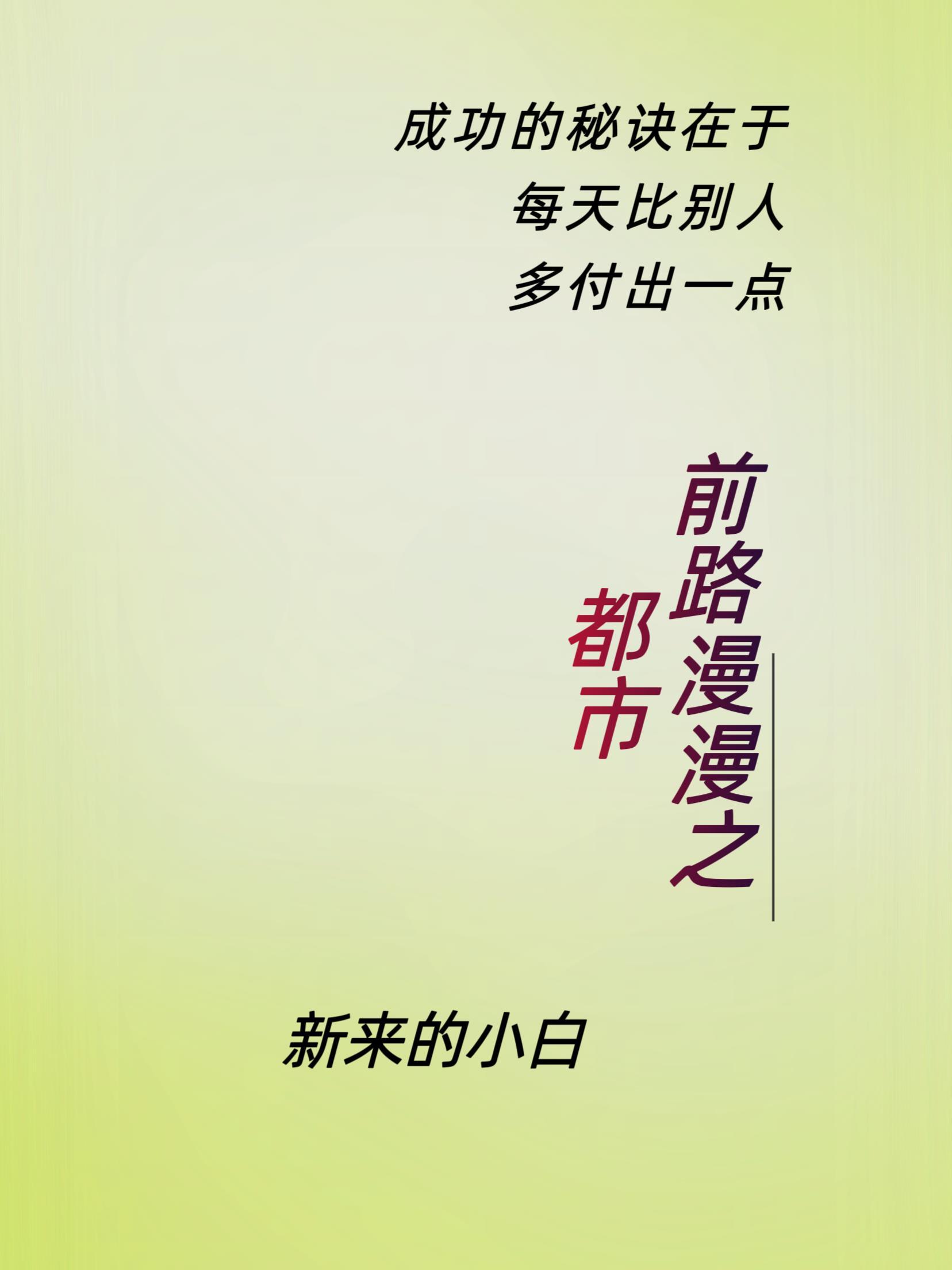极品中文>郎心似铁电视剧 > 第74页(第1页)
第74页(第1页)
又以为是幻觉,所有感官都变得虚无,只剩下一声声呼喊,第二次了吧,这样等待死亡是第二次了,似曾相识的气息,似曾相识的触摸,费尽力气一睁开眼,和上次一样,出现在眼前的竟还是上次那个人。
柏邵心惊喜的笑脸在那只医用小手电的照射下,有些让人觉得恍如隔世。“你忍忍,千万别乱动,我给你固定好背你上去。”
剩下的唯一一点力气我不想和他说话,只想打他,他握住我的手腕,力气不大,语气却强悍:“听话,别乱动,你的左腿可能骨折了,等你康复想怎么打我都行。”
我收回手,脾气竟然悉数消失。他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木枝将我的左腿固定住,布料在那上一勒,我疼得短促地叫一声。
“弄疼你了?对不起。”手电的光返回来,我才发现他赤着手臂,衬衫的两个袖子被撕掉,而我身上穿着的是他的外套和绒背心。
固定完受伤的腿,柏邵心把手电给我:“拿着。”然后背过身去,摆摆手指示,“上来,小心点。”
我呆愣攥着胸前的衣襟,眼前越发不清,痛觉神经慢慢苏醒,动一下就牵扯出几分疼。
他后退,借着微光拉过我的手搭在他肩膀。“别害怕,先回民宿,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再下山。”
我深知此时不该任性,乖觉地没出声,微微倾身伏上。
山路十分陡峭,确切来说,他脚下的根本不能成为“路”,而是碎石子和湿滑的草地,我紧紧抱着他的脖子,什么疼,什么苦,通通抛诸脑后,屏住呼吸,随之在林中摇摇晃晃,生怕他一滑,我俩一起栽进山沟里,原来人的求生意志只是一种本-能,纵使躯体千疮百孔,也不想轻易送命。
手电照着崎岖不平的小道,他背着我终于来到一条石板铺成的山路。
我暗暗松口气,知道小命保住渡过一劫了,一股压制已久的邪火涌上头顶。
“为什么救我?”
柏邵心顿了顿,微喘着:“在公,我是医生,救人是天职,在私,你是我的女朋友,就算用我的命来换你的,也值得。”
泪水直接从眼睑滴落,我低头在他肩膀上蹭干湿湿的睫毛。“女朋友?见不得光的女朋友?”
我不知道柏邵心内心在挣扎什么,隔了大概两分钟,他吞吐地说:“瞳瞳,我……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嫌弃你,我会永远爱护你直到我失去能力的那天,所以,千万别想不开做傻事,就算你被邵言…………”
我听的云里雾里,难不成他以为我的伤是被柏邵言虐-待的?“柏邵心,你只要告诉我,你爱我吗?”
几乎没有犹豫,立刻回答。“爱。”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柏邵心有点委屈地反问我。
我不顾脊背的擦伤,狠狠锤他:“放我下来!大骗子!大骗子!”
“瞳瞳,别——别乱动,会伤到腿——”
拳头上突然粘上湿湿黏黏的东西,我把手电的光移上一点,惊叫出来——竟是鲜血。
“出血了——”我不敢再碰,手臂耷拉在身体两侧,“你肩膀有伤——”
柏邵心把我颠了颠,放稳一点,丝毫没影响他爬山。“没关系。”
我方才撒泼似的打他,他没叫疼,却在担心我的腿,鼻腔里再次涌出一团酸涩。
“事到如今了,你为什么还要骗我?柏邵心,你说的爱,就是一次次把所有的事隐瞒起来,藏进肚子里,任谁都无法信任?我要是知道你结婚了,我一定不会……”
痴心错许。
柏邵心突然停住脚。我抬头,用手电照向前方,原来已回到民宿,终于等到有机会摊牌这一刻,一切纠葛可以就此有个了结吗。
“谁告诉你我结婚了?”
我抽下鼻子。“你还想否认?”
他没有走进民宿,而是转了下头,冷声再次问我:“谁告诉你的!瞳瞳。”
“你的好弟弟!”我不甘示弱,也冲他吼。
柏邵心深呼吸一口气:“他说你就信了?那如果我说我没结婚,你信不信呢?”
什么东西轰一声炸开,内心开始动摇,信,不信?到底谁才是大骗子?
他没有结婚么……
回到房里,柏邵心把我放在床-上,翻箱倒柜找到一个急救箱,从我包包中拿出一套干净衣服,准备就绪,便过来要脱我身上的外套和绒背心。
我瘪着嘴,死拽紧衣襟,说什么也不肯。
“害羞?”柏邵心拈着棉签蘸了下酒精,用典型医生看到矫情病人时那种眼神,“你身上我哪里没仔仔细细看过,还害羞?”
他在“仔仔细细”上加了重音,我败了,讪讪松开手。
新伤加旧患,我不敢去看自己的身体,闭上眼睛承受一阵阵皮肉之痛。
“啊,啊——”我缩着肩膀凄嚎,“你轻点行不行——”
柏邵心正擦拭我手臂伤口上的泥土,责怪地看我一眼。
我叫屈:“真的很疼。”
“我知道你疼,但没办法,伤口必须清理干净才能包扎。”不顾我的求饶,他抻开我蜷成一团的手指,握住,方便他摆弄伤痕累累的手臂,这厮不但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姿态,竟还噗地笑了,“你这么娇里娇气地求我,会让我自然而然联想到你被我欺负时候的样子。”
“柏邵心!”我喝道,但是看到他扬起满是真诚的眉眼,又被柔情似水的眼波电的一塌糊涂,羞耻之心让我把脸转到另一边,“请你自重。”
他叹口气。“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邵言什么时候告诉你我是已婚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