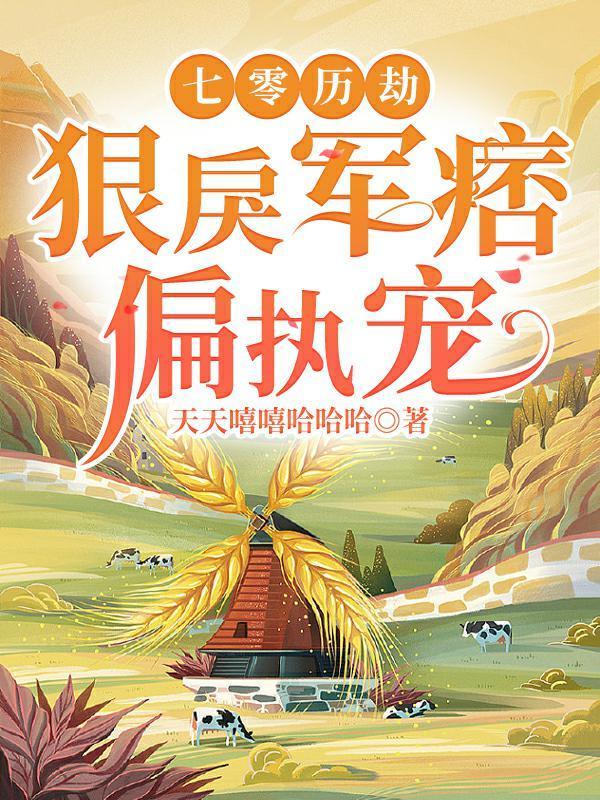极品中文>蒙尘珠泰剧电视剧全集免费观看 > 第89頁(第1页)
第89頁(第1页)
「傻珠兒,怎麼硬要和自己過不去呢?和我說說,夢到甚麼了?說出來會好受一點。」
珠碧極力忍著眼眶中呼之欲出的淚水,到了最後忍不住了,只能張開嘴一同呼吸,才能把眼眶裡的濕意給硬生生憋回去。
過了好久,珠碧才克制好情緒,哽咽道:「我又夢見我初到南館的時候了……」
他瑰麗絢爛的一生,都終結在人牙子把他裝進麻袋的那一刻。
在一片黑暗與顛簸之中,年幼的朱雲綺既無助又絕望。他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折往何方,只知道從今往後,他再不能夠承歡父母膝下,做一個無憂無慮的孩子了。
等重見到光的時候,是麻袋被解開的一刻。
他看見了姚鴇頭居高臨下地審視著他,而後,當著所有人的面,撕開他的衣裳,打開他的腿,在那隱密之處戳戳弄弄,像審視一件貨物一樣擺弄他。
「是個好貨,不錯。」這是他聽到姚鴇頭說的第一句話,至死也不會忘。
姚鴇頭掏出一張銀票給了那幾個人牙子,清楚地記得,那是五十兩銀。
五十兩銀,這就是他的命。
人牙子走後,姚老鴇慢悠悠地取來一根又黑又粗的鞭子,纏在手上試了試韌勁,他對朱雲綺說的第二句話是:「先叫聲爹爹來聽聽。」
朱雲綺只有一個疼愛他的爹爹,他怎能喊別人爹爹?
雖然害怕,但朱雲綺不肯從,他顫顫巍巍道:「我爹爹又不是你,為甚麼要管你叫爹爹……」
咻——啪。
狠狠的一鞭不由分說地咬上朱雲綺的身體,朱雲綺痛得大哭,而後姚鴇頭道:「等你甚麼時候叫了,我就甚麼時候停下來。」
幾鞭子過後,渾身是傷的朱雲綺終於受不住疼痛,哭著喊出了那聲爹爹。
鞭子打碎了他的前塵過往,葬送了他的錦繡前程,熄滅了少年人眼底炙熱跳動的光芒。而之後非人的調教、殘忍的折辱壓迫,更是摧毀了他所有的自尊。
他想過逃跑,想過自殺,卻最終都沒能如願,只能換來更加歹毒的毆打與懲罰。
雲霜被掛在南館外那棵樹上只熬了一夜,朱雲綺當年卻整整熬了兩天。
他已記不得那兩天有多少男人凌辱過他,只記得最後自己精疲力竭,終是喊出了那一句:我從了。
此話一出,自此,世上再無朱雲綺。
作者有話說:
小珠珠是個級抖m啊~其實,他是有輕度精神病的。
emmm…在那樣的地方呆久了多多少少有點精神障礙。錦畫也有,他有暴躁症。
下一章讓帝君安♂撫小珠珠~
第46章真邪夢邪
燭火如豆,明明滅滅地搖動,映照出一片昏黃。
壓抑著的哽咽聲如柄鈍刀一下下地磨著人的心,珠碧倚在靈鷲懷裡,重重地吸了吸鼻子。可無論如何,他也控制不住語調里的哽咽聲:「我告訴過自己不能哭的……可我……」
在南館,珠碧從不曾在恩客與其他妓子面前哭,事實上他做這噩夢不是第一回了,往往一個人睡時他都會跌入這個夢境之中,掙扎著醒來,小九也睡熟了。身邊空無一人,他只能呆坐在床頭,望著燭火枯坐至天明。
他難受,卻不能哭。
有太多雙眼睛骨碌碌地盯著紅牌名妓,費盡心思地要扒拉他們的把柄與軟肋,好拉他們下來。所以這麼多年,珠碧早已學會怎樣控制自己的情緒,至少不能哭出聲來。
他想哭的時候,就仰頭瞪著帳頂,張開嘴同鼻子一起深深呼吸,這樣就能不發出半點聲音。等到第二天南館開門迎客,他就又是那個婀娜嫵媚,風情萬種的名妓。
可這樣的辦法,到了靈鷲面前卻顯得不那麼好用了。靈鷲是第一個闖進他生命中,張開雙臂緊緊抱住他的人,他沒有辦法在他面前再披上那層堅硬的盔甲,故作平靜。
靈鷲抬手金光乍泄,登時滿室浮起淡金色屏障,將室內與外頭天地徹底隔絕,他嘆了口氣,道:「這裡不是南館,沒有人能聽到了。珠兒,哭出來罷。」
哭出來罷,放聲哭出來罷。連哭也要硬生生忍著,也太可憐了。
珠碧再忍不住滿心怨恨與委屈,伏在靈鷲肩頭放聲痛哭起來。
哭得天也昏,地也暗;哭得喉嚨喑啞;哭到靈鷲也心肺俱傷,衣襟盡濕。
窗外寒風席捲,嗚咽著敲打窗欞。想鑽進來霸占這一方溫暖之地,而靈鷲施下的屏障牢不可破,所以便是任那寒風再囂張,也無法侵略分毫。
珠碧哭幹了眼淚,聲音漸漸息了,此時一抽一搭地打著嗝,他尤不安心,一遍一遍地問著:「這是夢嗎?」
靈鷲不厭其煩地一遍遍答:「不是。」
珠碧搖著頭不肯相信,拽過靈鷲的手放在自己身上:「打我罷,讓我疼……讓我心安……」
對珠碧來說,疼痛能生出安全感,能讓他深刻意識到自己被擁有,被支配。
而且若真的是夢,夢中人是感覺不到疼痛的。如果能深深刻刻痛一回,至少能確定這一切不是一個美麗的夢。
可靈鷲又怎捨得動手打他?
見靈鷲不肯動手,珠碧愈發覺得一切都不真實,掙開靈鷲的桎梏,抬手竟發狠地朝自己臉上甩耳光——
「珠兒!不要胡鬧!跟我發瘋是不是?」靈鷲氣急敗壞地揪住他自殘的手,怒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