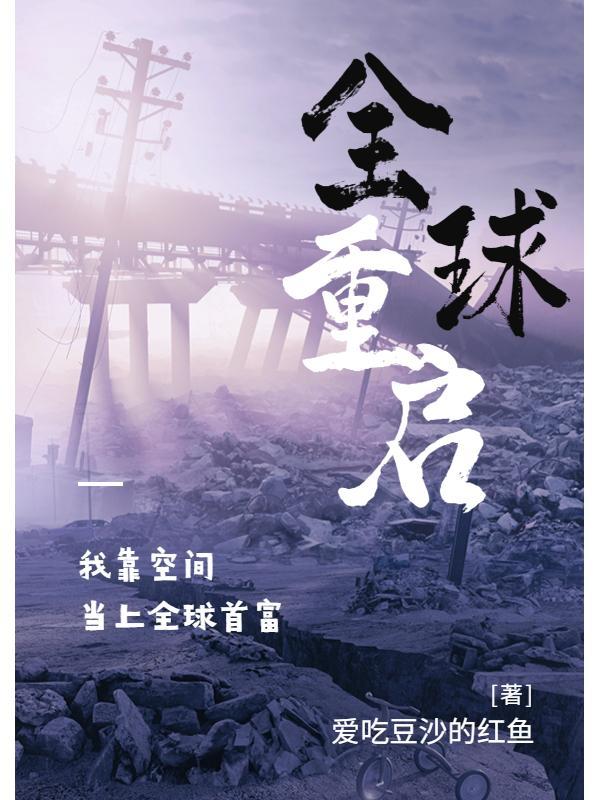极品中文>秦凤药传奇男主角是谁 > 第28章 还你一局(第2页)
第28章 还你一局(第2页)
“生意不好,爹娘去亲戚家了,须有一段时间不回。我也闲。”
大牛向灶台中加柴,有些丧气的样子。
“说起来,少见伯父伯母,总是你独自打理生意。”凤药与他闲聊,大牛低着头不接话。
两人静了半天,大牛抬头突然恳求她,“别惹王寡妇了,你斗不过。”
“再,再说,也是你对她不住在前。”他声音逐渐小下去,仿佛知道些什么。
“这话说得不公,我并没有什么对不住她的地方。”凤药说得冷淡。
打从来到这个小镇被王二索要财物,她一直被动应对人家的挑衅。
顶多泼了三天粪,教训对方一下,并未对她造成任何实际伤害。
王二起了淫心,企图污辱小姐在前。
那是在要三人性命。
小姐失了清白,凤药与胭脂必要陪葬。
现在只后悔,为何没有一下将其治死,留下这么大一个隐患。
大牛长叹一声,“总归是我多嘴,都怪我。”他说着扇了自己一巴掌。
“小弟原谅哥哥吧。”
凤药拉起大牛,“大牛哥这不怨你。小镇上能有这样的祸害而无人治理,才是根本的错。”
大牛怔怔看着她,仿佛从未想到过此节,他无奈地长叹一声,离开了。
时至傍晚,凤药站在门前张望几遍,才把胭脂盼回来。
远远瞧着,她像牵了头小牛犊子。
走得近了,才看到那狗儿长得如棕色雄狮,壮而高大。
狗头一圈生着浓厚的鬃毛,人立起来如健壮男子。
嘴上套着笼头,涎水不停流下来,只看外形便知其恶。
“让开。”胭脂走得一头汗,“这狗儿现下只认得我。”
“什么狗,这么厉害。”
“狗场说是獒犬。不是我们这边的种儿。专为护院准备,斗得赢野狼呢。”
“在那边光是听我指令就花了半日,这狗得从小养,你只要成年狗,人家租给咱们了。”
“狗主说了,它吃得多,我们算替他养几日,省下不少嚼吃,租银倒没几个钱。”
那狗很沉稳的样子,将它拴在院内,它只向地下一卧,闭起眼睛。
一群鸡跑过去,凤药倒吸口气,刚想喊,大狗一只眼眯起一条缝,瞄了一眼并不理会。
胭脂很得意,“主人家说了,这东西灵得很,能闻得出人的恶意。只要不是来做坏事,它轻易不会叫。”
“你别近它就行了,咬到了,不撕掉块肉不会松口。厉害的给咬到喉咙,立时就死了。“
晚间两人将狗拴在铺子里,松了笼头。
王二他娘晚上的确又过来了回,隔着墙只听得隐约像有野兽的喘息呼噜声。
她拿砖头垫着脚向院内看,先闻到一股臭气扑到脸上。
再低头,一双绿油油的眼睛,与她只有几拳的距离。
原来那畜生听到有声音,便两爪搭墙,立了起来,并未吠叫。
女人吓得半条命几乎丢了,一下从砖上跌下来,脚踠子顿时肿得老高。
她恨得心中暗骂对方小兔崽子,不得好死,将对方祖宗骂个遍,一瘸一拐不甘心地回家。
第二天,她气不过又来捣乱,拄着拐大大咧咧坐在桌前。
“你们这些外乡人在此做生意,也不本份点,汤里不干不净,谁来吃?”
桌前早就坐满客人,并未有人搭理她。
胭脂早就等着她来,端起一碗汤走到她面前,撇嘴笑着说,“你说汤不好,咱们白送你一碗好好尝尝。”
一边说,一边将一大碗半热的羊汤,兜头盖脸淋下去。
汤汁顺着寡妇头脸向下流,葱花挂得满脑袋都是。胭脂接着说,“你一个无儿无女的妇道人家,心地恁地狠毒,向我锅中投放垃圾,毒死我看家护院的狗,你儿在地府等你多时,你怎地还不去寻他团聚。”
“好个王八羔子!”女人怒火中烧,指着胭脂鼻子尖骂,“不知死活的小乞丐,你死八百遍我儿也不会死,你等他从野人沟带人来绑了你,烧了你的店,你才知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