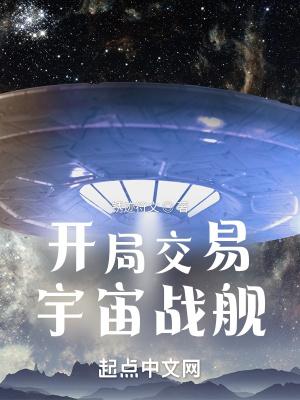极品中文>背叛电视剧在线观看免费完整版 > 第16頁(第1页)
第16頁(第1页)
漆黑的髮絲仍在發力,就在它將我的整隻手臂攪成肉泥前一刻,被我護在懷裡的直哉發出了啼哭。
混亂中,他四散的咒力有一縷恰巧灌入護符,一時間被染血的護符光芒大盛。
最後的咒力化為爆發的火焰,它救下了我的胳膊,暫緩了咒靈的攻擊勢頭。
「快跑啊!叫人過來!」
我趁亂再次激活「未盡之言」,使出最後一點力氣,將身邊的阿玲狠狠地推了出去。現在咒靈的目標是抱著直哉的我,阿玲比我更熟悉禪院家的地形,她先逃走才有叫來後援的可能。
就在髮絲扎入我血肉那瞬,咒靈意味不明的尖叫化為女人的哭喊,清晰地傳入我的耳中:
「我只是想讓直毘人大人開心而已,我想要他愛我。我吃了噁心的藥,身體腫了起來,好痛、我變得好醜。他們剖開我的身體,取走我的孩子,卻沒有人記住我……」
「他還是惦記著別人……誰都不愛我,誰都不在乎我,好痛苦、好痛苦、我後悔了!我要報復他!!我要帶走那個孩子!」
強烈的情感中,一半是對直毘人的愛,一半是恨,但痛苦卻只留給了自己和孩子。那因愛歇斯底里的姿態,逐漸和我記憶中另一道身影重疊。
尖銳的疼痛令我眼前發白,冷汗早已濡濕我的鬢髮。但此刻,比起將被殺死的恐懼,我感受到的卻是憤怒。
為什麼?
若不是啞巴,我多想像阿玲一樣發出質問。
她們是不是總喜歡這樣?把孩子當成討好丈夫的工具生下來,如果沒能從男人那裡得到想要的東西,就遷怒給自己的孩子。
從來沒有問過孩子的意願,想不想出生,想不想吃藥,想不想開口……
就這樣剝奪了他的想法,現在連生命也不放過了麼?
憑什麼呢?
強烈的情緒使我忘記逃跑,放棄求饒,只想一股腦釋放出現在所有的咒力,將這個陷入癲狂的女人摜倒在地。
因疼痛而抽搐的手指像雞爪一樣收縮。我咬緊牙關,將洞開的掌心狠狠一攥,把火焰中倖存的頭髮用力拽向我的位置。
而在我的周圍,被黑髮打散的黑影並未散去,它們悄悄化為彌散的大霧,將我和咒靈團團圍住。
相傳天元年輕時曾四處雲遊,為村落張開結界隔絕妖魔的襲擊,他的出現是祝福也是詛咒,結界內聚集的高濃度咒力喚醒了生兒的潛力,也招來了死亡。
這慈悲的僧人不忍幼子死去,徹夜為其祈福誦經,他強烈的願望催使咒術有了的用途:
不僅僅將咒力封存,還要更精密地操控結界內咒力的流動。
響應我的願望,狗死亡那天現身的大型結界再次現身於此。
拔地而起的漆黑牆壁隔絕了外界的一切,明明是一片黑暗,我卻仿佛置身夏夜河畔,在觸、手構成的芒草間看見了飛舞的螢火。
我看到了。
那就是我想要留下來的,隨直哉咒力溢出的生命力。
他將臉頰挨上我的染血的手臂,氣息微弱,覆蓋在身上的曦光仿佛隨時將要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