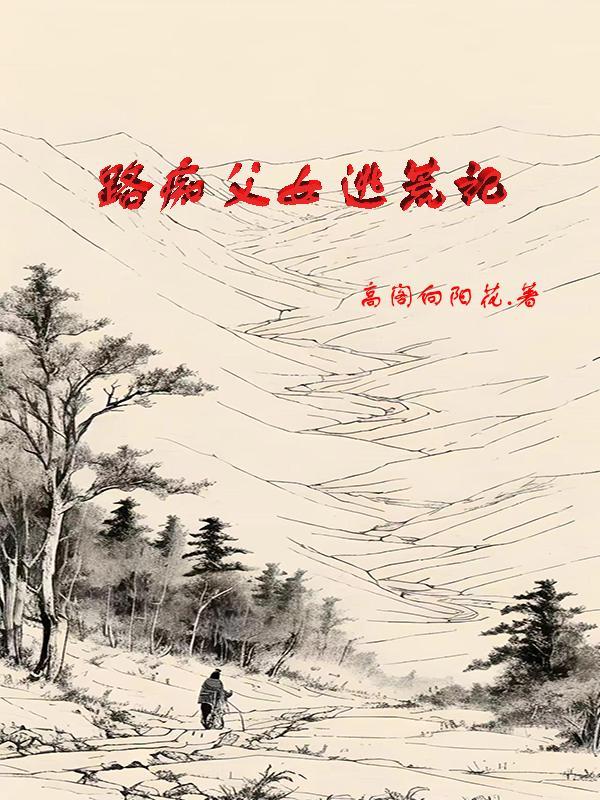极品中文>师父给你小心心全文免费阅读笔趣阁 > 第30章 知晓重生之事(第1页)
第30章 知晓重生之事(第1页)
月升日落,一日很快就过去,
萧烨整日呆在书房里,心绪有些不宁,
对于接下来的事,他有些按耐不住,想要快点进行下去,待把事情解决好,他还有重要的事去做。
他缓步出了书房,朝自己的卧房走去,看着无尽的黑夜,心里挂念着给他留书出走,现在不知如何的人,
除了回京的日子,只要身在庄里,他每天都能看见那道纤细窈窕的身影,
她从小在这里成长,以前就算偷偷跑去城中,无论如何天黑之前都会回来,这还是她第一次在外头过夜,不知她是否习惯?
榻上,萧烨带着对褚颜的挂念,渐渐跌入梦乡,
梦境里,萧烨看到一群人挟持住褚颜,他们把锋利的刀架在她的脖颈上,她细白的脖子被锋利的刀锋划破,殷红的血液滚落下来,滑过她的颈肩,那些人以此威胁他自断手筋,
为保她的性命,他迫不得已,只能答应自断手筋,见他妥协,那娇俏的身影拼命的喊着不要,他举起刀子准备对自己动手时,褚颜已先他一步对自己动了手,她对着架在她脖子锋利的刀锋用力一抹,鲜血顿时喷涌而出,她的身体被一个络腮胡子踢了一脚,跌落悬崖,
见褚颜跌落悬崖,他跑向崖边嘶喊着,可他撕心裂肺的叫喊声,阻挡不了她往崖下坠落的身子。
然而就在他无法面对失去她的悲哀中时,一把锋利的大刀从他后背刺入并穿过前胸,络腮胡子大笑着把刀抽出,他身体也朝崖下坠去。
坠落中,他拼尽全身之力加快下坠的度,如愿抱住了先他一步坠落下来的人,这时的颜儿已是弥留之际,他也好不到哪儿去,浑身是血的两人相拥着往崖底坠去,那被鲜红血液浸湿的衣衫,分不清是谁的血,
在他弥留之际,他抬起手想再最后摸摸她的娇颜,可还没碰到他的手就已垂下,几息后,她也缓缓闭上眼,也已气绝……
萧烨反复重复着这梦境,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他腾的一下坐起身来,惊呼一声,
“颜儿,”
萧烨摸了一把自己的胸前,是湿的,他低头一看,白色的里衣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血渍,打湿他衣衫的不是他们的血,而是汗水,他的前胸是好好的,没有受伤的痕迹,
看着窗外的夜色,还有现在坐在榻上的真实感,萧烨摸着完好无损的胸,难道刚才只是一场梦!
可那真的只是一场梦吗?那么清晰的痛感,无论是身体还是心,到现在还能真切的感觉到心痛。
自己和颜儿被血浸湿的衣衫,他最后想摸摸她的脸还没摸到就垂下的手,她缓缓闭上的眼睛,
萧烨仰起头,紧抿薄唇,静静感受着心里泛起的阵阵疼痛。
片刻后,萧烨睁开眼睛,眼里溢满了浓浓的杀意,
那个狂笑的络腮胡子,他叫刘谦雄,是一个不入流的帮派帮主。
起初看到那张画像时,以为颜儿可能是偷溜到琼城玩的时候认识他的,两人有过节颜儿才会想杀他,可现在仔细一想,萧烨觉得这样的想法说不通,
以前她不爱练功,只想出去玩,她每次能偷溜成功,都是自己睁只眼闭只眼的结果,
因为不放心,所以褚颜每次偷溜出去都会有人跟着,她在外头生什么事暗卫归来都会禀报,期间从没听说过她和刘谦雄有交集,
能让一个人恨不得杀掉对方,其中生的一定是大事,若真的生了什么事?暗卫不可能不知,再者按照颜儿当时的性格,摔跤摔疼了都会跑到他面前来让他说几句好听的话以示安慰,若真的生什么事,她不可能默默的受着一言不。
思来想去,萧烨想到了小时候听过的虚无缥缈的轮回说法,有一种说法叫重生,
萧烨身子一僵,得到一个他难以置信的结论,难道他的颜儿……
思及此,萧烨觉得自己可能是疯了,那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传说,如此令人匪夷所思之事,怎么可能是真的?还那么巧的生在颜儿身上,
不过很快萧烨又否决了自己的否认,她心里藏着的事和她的变化,
若真是这样,萧烨觉得很多事情都说得通了,
颜儿落水后突然去了后山练功,当时他还问为什么突然间想好好练功了?她说做了一个梦,虽然当时只说了三言两语,但说的梦境和今天他的大同小异。
当时她说梦境时眼里流露出的哀伤,萧烨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他只当她是因为差点溺毙才历经生死而害怕,
她落水醒来后抱着他大哭的场景,难怪她会那么伤怀,她是刚历经生死不假,只是不是溺水,而是刚经历他们前生生命最后时刻,她的那一场大哭,不是因为差点溺毙的害怕,是跨越了一世生死后的失而复得。
难怪她会在没见过刘谦雄的情况下就对其恨之入骨,也知晓言十一是叛徒,原来这一切皆因前生之事。
她每次说起来生时,难怪自己的心会那么痛,原来那是他前生弥留之际想对她说却未说完的话。
萧烨沉浸在悲伤的思绪里,忽听院中有轻微的异动,他静静坐在榻上,几息后一道黑影无声无息从窗户闪进来,单膝跪着萧烨榻前,
“公子,你交代之事已经查清,画像上的人叫刘谦雄,创立了一个叫铁斧帮的帮派,盘踞在江城,平时鱼肉乡里,当地官府为中饱私囊,和其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当地百姓对其敢怒不敢言,”
榻上之人一言不,对单膝跪地的人挥了挥手,瞬息间,黑影消失。
萧烨无力的仰起头,任由疼痛的感觉从心口蔓延至四肢百骸,
颜儿在几年前就知晓前生之事,而他时至今日才知晓,萧烨心中又痛又苦涩,要是他在她之前知晓多好。
萧烨从榻上下来打开房门,看着远处慢慢变亮的天色,暗自吸了几口气,露出一抹苦涩的笑,
他的颜儿真傻,这几年从没告诉过他,或许她是无从说起吧,如此匪夷所思之事,她是怕说出来他也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