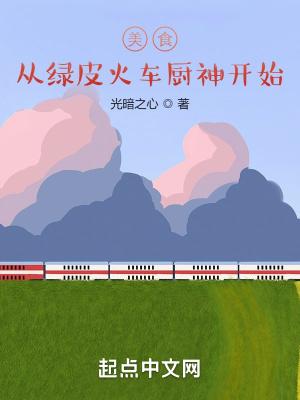极品中文>团宠娇气美人是满级大佬 > 第61頁(第1页)
第61頁(第1页)
但是牌牌!!
說的話除了在醫院賤嗖嗖模仿那次,和說秋紀陶實力沒有他厲害,這兩次聽懂了之外其餘都不是很懂。
「玩可以懂嗎。」
見他拿出牌,瘋狂點頭,從剛見面牌牌就說教自己玩牌,現在才終於有了實際性。眼睛亮晶晶地衝著撲克牌招手,示意他把耳朵湊過來。
怕他再廢話,揪著他耳朵,唇瓣湊近悄悄說,「我看到你和洲洲一樣,是長頭髮。」
就在剛剛失去世界的失重地里,他看到了撲克牌的真實面容,可惜現在不記得了,只記得他的頭髮。
席洲鬆開他,見他望著自己,手指在唇瓣上微碰一下,輕「噓」了一聲,沖他眨眼。
撲克牌被他蠢萌到了,搖頭輕笑,真是個不經世事的小羔羊啊,入了遊戲場這個大灰狼的口,是會被吞得一滴不剩的。
……
……
「和雅姐姐,那些人是誰啊?這裡是什麼地方?」爆炸聲鬧劇落下後,三個女人進到一個房間。女孩好奇逮住蘇和雅問來問去。
和雅姐姐表面上看著最冷漠不過,但其實很善良的,剛剛上樓梯她差點摔倒還扶了自己一把。
而且倆人年齡相仿,只要點燃一點的火星子就能燎原,燒了這無邊的黑夜,照亮前方的道路。
與和雅姐姐在一起那個女士看起來不好接觸,特別是對上男士,恨不得上去啃食他們血肉,一點也不誇張。甚至在看向自己時都有一種審視感。
蘇和雅把這裡是什麼地方,所有的副本和線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告訴兩位女玩家。
她知道這個副本玩家之間自相殘殺沒有用,只有聯手才能走出去。
「我知道的只是一知半解,真正的線索還是要靠他們。」他們,蘇和雅說得非常清楚。
「女性什麼時候才能獨立起來,靠自己不靠男人!」許炫嗤笑,語氣中充滿著輕視與悲哀。
她不是沒有反抗過,說來也可笑,這些反抗都是被同性給壓下了。
向來女性便是低人一等,無數的女人依附著男人而活,從心理、行為上提高他們的地位。
正因這份想活命的尊崇感才讓男人們覺得女性離了自己什麼都不是,才不把女性當人看,當做為所欲為任其擺布的泄憤工具。
晏書察覺到覆蓋在自己手背上面的手輕微顫抖,抬頭看著蘇和雅。
蘇和雅眼神出神,不知道想到了什麼,眼神抹上了淒涼。
晏書從她眼神中看出了被無數荊棘包裹的人兒,刺離她皮膚只剩不過三厘米的距離,她不敢掙扎只敢乖巧不動從而保護自己。
蘇和雅抓著床邊的指尖開始泛白,深吞吐幾下緩解了情緒開口,「有,有人可以掌控男性。」
可有什麼用?她們比男性還要恐怖惡毒,人性都是如此。無論誰掌控這個世界,只要不是自己都覺得不公平。
許炫見她表情痛苦沒有再問。
蘇和雅眼皮輕顫,沒有過很長時間睜開眼睛,臉上掛著笑容,開始一個個介紹四位男性,仿佛剛才的事情不曾發生。
許炫趁著她們說話期間在屋子裡找線索。
現在沒有什麼危險能給她們喘氣的時間,也就任由著她們說話,小女生湊到一起塊談天說地的很正常。
「鏡子?」許炫突然的聲音吸引了兩位女生的目光。
許炫把反著放在書架框裡面的鏡子反過來,擺在柜子上面,從鏡子裡面看到蘇和雅和晏書向這邊走來的畫面。
「這鏡子怎麼是反著?」
蘇和雅走過來聽到她的嘀咕詢問,「有什麼問題嗎?」
許炫比她們多了二十多年的經歷,此刻不自覺以長輩的身份自居,「我們比較封建,晚上只要不是牆鏡都會背過去,怕招惹到不乾淨的東西。」
蘇和雅和晏書對視一眼,她的意思是懷疑,這個屋子裡有……
「啊!!」晏書一聲驚呼把倆人都嚇了一跳,看到面前鏡子裡面的畫面,頓時覺得寒氣四溢,無形鑽入身體內,讓她們覺得骨頭都被寒冰凍著。
一張臉占滿了鏡子,待看清楚後,三個人同時鬆了一口氣。
「以後別大驚小怪的。」許炫說了一下晏書,彎腰觀察鏡子裡面的東西。
蘇和雅拍拍晏書的肩膀,「習慣就好,遊戲場就喜歡出其不意地嚇人。」
晏書定睛一看發現裡面是個可愛精緻的小木偶,反應過來道歉,「叫快了不好意思,剛才看到鏡子裡面沒東西,突然之間有了嚇一跳。」
鏡子裡面是個身穿著小洋裙的木偶人,仿佛是出現在鏡子面前在照鏡子,做木偶的人手藝很好,惟妙惟肖地像個真人,後腦勺扎著兩個小揪揪,在盯著她們看。
經歷了以往遊戲場的恐怖,這根本就不算什麼。
許炫把鏡子拿起來仔細端詳,想看看鏡子裡面出現的木偶是在哪個方向。不是鏡子裡面的,剛開始看是沒有的。
當她拿起來之後,發現鏡子裡面出現了一些不同模樣、裝扮、甚至於連表情都不相同的木偶人,她們不過五六歲,是正常平均孩童般大小,有些邊緣有些只有半張臉一隻眼睛一捋頭髮,卻擠滿了鏡子,多餘的好像溢了出來。
蘇和雅一直跟隨著她的動作看向鏡子裡面,看到木偶人本能扭頭看向房間內,沒有。